讓我們一起傾聽親歷者的故事,感悟歷史中的人、人的歷史……
來源:摘自《絕唱老三屆》 肖復興 著 中國華僑出版社文章版權歸作者所有,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數百萬知識青年懷揣理想和激情,奔赴祖國的農村和邊疆。
40年的光陰,讓「老三屆」作為一個特殊名詞載入了史冊;40年的光陰,讓當年的老三屆人如今霜染兩鬢。面對歷史,重新回顧青春的歲月,他們可能會為自己曾經有過的可笑的幼稚和真誠,以及種種無可挽回的閃失和局限而感慨……但是,僅僅沉浸於懷舊的情緒之中是不夠的,那會阻礙我們真正地走進歷史,容易使回憶走形甚至失真。

「回憶更應該是一種思想、一種觸動,而不止於撫摸。」老三屆的命運是與共和國的命運膠粘在一起的,他們的經歷,他們的痛苦,他們的反思,是下一代的營養,也是這一代人特有的生命價值。肖復興的新著《絕唱老三屆》讓我們重新審視已經步入退休之年的這一代人40年的生活軌跡。
——編者
陳光順和童建華是1969年從上海來的知青。那時,陳光順是隊上的統計,後來又幹過機務,最後是副隊長。人長得高大挺拔,面龐英俊。記得隊上曾經排過樣板戲《紅燈記》,幾乎眾口一詞,李玉和非他來演莫屬,儘管他一再推脫說自己根本不會演戲,大夥依然非拉他上陣不可。雖然他一口上海腔唱得差些,但他的扮相要遠遠賽過胖得有些臃腫的浩亮,上台一亮相,滿堂喝彩聲。
那時,童建華先後幹過農工、機務,又當過文書。她人長得苗條又秀氣,身材尤其好,個子高高的,腿長長的,即使厚厚的大棉襖遮住了漂亮的三圍,也遮不住她天生的美麗。而她的性格比她人還要美麗,極其溫和得體,有一種在當時難得的書卷氣。她的字寫得和她人一樣的漂亮,一看就知道從小受過良好的教育和訓練。她不多言多語,幹活任勞任怨,從不怕吃苦,和有些嬌氣的上海女青年大相徑庭。
如果說陳光順像是北大荒上一棵挺拔的白楊,童建華確實像是一株秀美的白樺。因此,當他們兩人相愛了,所有的人都覺得是天設地造的一雙,都為他們祝福。
其實,戀愛對於童建華來說,是當時一種無奈的選擇。童建華從心裡絕不想在北大荒找對象,更不想在北大荒結婚。她出身在一個知識分子的家庭,讀書一直是她未泯的希望,尤其有了可以推薦工農兵上大學的消息之後,這種念頭便像燃起荒火般燒得心裡難受。以她幹活的態度,以她的好人緣,當然也應該包括她的好模樣,隊裡推薦工農兵上大學,自然推薦上了她。誰知,政審不合格,說她的父親有歷史問題,大學之門無情地向她關閉了。就是這時候,她相中陳光順作為自己的對象。人生失利之中,戀愛給了她溫情的撫慰和補償。
所有的領導都會喜歡像陳光順這樣的人,忠厚能幹又聽話,出身又是地道的工人,家裡家外光滑得沒有一點毛病。因此,他剛到北大荒不久就入了黨、提了干,成為了當時需要的典型。他像是一張白紙,任人在上面描繪當時流行的最新最美的畫面。這種畫面曾經使得他一度輝煌,卻在關鍵的時刻遮擋住了他的去路。推薦工農兵上大學,便沒有他的份,因為他是被培養的接班人,當然要留在北大荒發揮作用,他已經自覺地斬斷了上大學的念頭。
1976年,最後一批工農兵大學生的名額,像是旱天中稀少的雨點,童建華幸運地趕上了這列末班車的尾巴,被推薦上了哈爾濱的一所中專,學金屬專業。雖然沒能上夢中的大學,畢竟離開了北大荒,有了學上,也算是退而求其次吧。
陳光順為童建華送行時,—下子百感交集而無法言表。來北大荒7年,戀愛3年,感情同時融在這片土地和女友身上。他當然希望她如願以償,但又捨不得離開她。他慶幸她終於上了學,又為籠罩在自己身上一時的輝煌而脫身不得,痛苦得無處訴說。
幸虧這樣的日子並不太長,一年多後,「四人幫」被粉碎了,高考制度恢復了,陳光順考上了哈爾濱的中專,他欣喜欲狂,即刻打點行裝,奔向哈爾濱與童建華會合。
然而,他們沒有想到,相逢和讀書的喜悅還未過去,旋即颳起了知青返城風,而且越刮越猛,上海在向他們招手了。陳光順和童建華商量,他們這一屆學生畢業後全部都要留在哈爾濱,到那時再辦回上海恐怕就難了,他想退學回北大荒,再辦回上海可能要容易些。那麼,就得把可以到手的文憑丟掉。童建華支持了他,先回去一個人,總算先有了一線光亮。讀書和回家,是當時身在異鄉的多少知青心裡的兩大情結呀!
於是,陳光順和童建華再次分離。陳光順回到北大荒,農場已是面目皆非,知青宿舍人去屋空,一片淒涼。他知道轟轟烈烈的知青上山下鄉已經到了尾聲,只是,他不知道這個尾聲會綿延那樣漫長的時間,直到他和童建華進入老年。他不知道時代的震盪,只不過是輕輕翻過的歷史的一頁,而對於個人卻是整整一生。在歷史面前,每一個人都是這樣弱小和渺小。
別離之中,陳光順無所事事,他要做的除了思念,就是等上海的調令。這兩樣東西都在磨他的性子,天長地闊,大雁南飛,草甸子上荒草搖曳,七星河水水流清瘦,北大荒寥廓蒼涼得讓他想落淚。
1980年,陳光順終於等到了上海的調令。離開家11年之後,他又回到家了,走了一個圓圈,重新回到了原來的出發點上,青春已經和他揮手告別了。
單位先派他到九江生產第一線,一干就是5個月。在這5個月中,童建華也從哈爾濱畢業,辦不回上海,便先辦到了鎮江當老師,總算離上海近了許多。即使是依然有着兩地相思,兩人的心裡卻都有一種苦盡甜來的感覺,充滿着對未來新生活的憧憬。
誰想到,5個月後陳光順回到上海,迎接他的卻是禍不單行。因為他這5個月是住在九江傳染病醫院對面,竟染上了肝炎,回上海不久便住進了醫院。而童建華總鬧肚子疼,單位的醫生並不給她開病假,只是給她開點藥。等到她疼得躺在床上直打滾被送進醫院,已經晚了,子宮腫瘤,第一次開刀取出瘤子依然還長,只好第二次開刀摘除了子宮。起初,童建華埋怨是單位的醫生給耽誤了,後來她明白了,在北大荒,天寒地凍又潮又濕,她太年輕,幹活又太不惜命,病已經潛入她的身體裡,長年累月已經無可奈何了。
這對思念多年的戀人,終於從北大荒回到上海了,卻是咫尺千里,躺在各自醫院的病床上,對着皓月一輪、明星萬點,寄託苦澀的相思。
他們結婚是1985的春天,這時陳光順33歲,童建華31歲。童建華很愛並感激小陳,手術和激素藥物的後遺症,使得她明顯地發胖,再不像以前那樣苗條漂亮了,關鍵是子宮的摘除,使她再無法生育。可是陳光順毅然和她結婚,他只說了這樣一句話:「我愛她。」便不再說什麼。
但是,愛情同時也面臨着考驗。結婚之後,他們一直擠在陳光順的家中。一間房子,前有父母,後有弟弟,他們被擠在中間。在大上海的新生活,就這樣開始。
只是這一代人已經學會了吃苦而不訴苦,我們曾經是自願才搭乘上這列轟轟烈烈的時代列車的,當這列列車轟隆隆地駛走之後,我們被甩了下來,被摔傷,是必然的事情。所以,我們吃苦而不訴苦,因為我們知道訴苦不會得到人們的同情,下一代會覺得那些苦只是我們自找的,誰讓你們當初自以為真的能會當擊水三千里?我們只能悄悄舔舐自己的傷口,讓它慢慢結痂,讓它在陰雨天時悄悄帶給我們陣陣的隱痛。
1986年,童建華從報紙上看到上海市教育局和人事局聯合舉行諮詢活動,解決兩地教師的分居問題。她從鎮江趕回上海,拉着陳光順到現場,想死馬當做活馬醫,試一試。他們的運氣真好,趕巧碰上人事局局長坐在那兒值班,聽了他們的申訴之後,非常同情這對坎坷中的患難夫妻,說根據他們的情況,童建華是完全可以辦回上海的,並告訴他們辦理調動的程序,要先由陳光順的上屬公司申報。陳光順請求局長:「您能不能幫我們寫個條子?我們好找單位的領導。」好心的局長幫他們寫了個條子。這張條子起了作用,單位領導再不推諉,立刻打電話給公司,公司立刻打報告向市里申報……他們不知道陳光順和童建華到底和市人事局的局長是什麼關係。複雜的問題—下子簡單化了。生活在給了他們那麼多磨難之後,終於向他們露出了笑容。
童建華回到上海,在一所大學的實驗室工作。曾經吃過苦中苦,她的工作是沒得挑。然而就在這時,陳光順家中後院起火。他的弟弟要結婚,惟一的一間房子,弟弟要爭着做新房,最後竟和哥哥爭吵起來。童建華夾在中間,非常尷尬難受,最後,兩人只得搬進了童建華父母的家,和兩個老人住在了一起。那是一間10平方米的西房,天天被曬得火熱,最惱人的是和老人的相處,老人原來都是單位的領導,自尊心很強,陳光順在北大荒也曾是個頭頭,自尊心也很強。幾強相遇,難免碰出火花。那一陣子,家冷冰冰的,下班回家,誰也不說話,父母看電視,童建華看書,小陳塞上耳機抱着收錄機聽音樂,每天如此,各就其位。
如果有個孩子,那該多好,就不會這樣死氣沉沉的了。童建華和陳光順都想到了孩子,沒有孩子的痛苦,此時才真正像撒在傷口上的鹽,在他們心裡隱隱作痛,他們誰也不說什麼,但比說出來還要疼。沒有孩子的家,像是沒有放鹽的菜,日子過得單調得要命。那一陣子,童建華和小陳有時下班後竟誰也不願意走進這個家門。
辛辛苦苦熬回了上海,為了什麼?付出了一張文憑、一個子宮的代價,又是為了什麼?他們曾經是多麼讓北大荒的老鄉們羨慕的一對,北大荒的磨礪卻讓他們的生活殘缺,內心永遠淌血。但即使在那些摩擦的日子裡,他們誰也不提孩子的舊傷疤,他們知道那是北大荒留給他們青春的紀念。
像許多從北大荒回到上海的知青一樣,他們勤勤懇懇地工作,老老實實地生活,他們失去了許多,但他們沒有太多抱怨,也沒有太多的感慨,他們知道無論怎麼樣,日子都像路一樣總是要走的,那麼就往前走吧。
這幾年,他們的日子過得很好,陳光順提拔到研究院當負責生產的院長,童建華當了實驗室主任,還兼任着學院的支部書記和工會主席,兩口子的工作更忙了。他們搬了新家,住上了112平方米的大房子,兩口人足夠寬敞的了。
從北大荒的青春時節一起攜手走來,竟然—下子走過了40年的路程。一天天的日子,過起來的時候顯得那麼慢,只有當它們被甩在了我們的身後,才顯得飛快。所有的一切,哪怕是痛苦艱辛的日子,也變成了美好的回憶。(摘自《絕唱老三屆》 肖復興 著 中國華僑出版社)
標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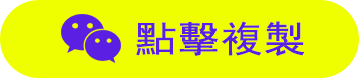




評論列表
情感分析的比較透徹,男女朋友們可以多學習學習
如果發信息,對方就是不回復,還不刪微信怎麼挽回?
如果發信息不回,怎麼辦?
發了正能量的信息了 還是不回怎麼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