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木是大二中文系的學生,屬於沉悶的性格,繁雜的迷離眼神總是四處游弋,極具戲劇天賦的它像崇尚天堂的膜拜着莎士比亞,每當興起,沉悶的表面即刻飛散,用普魯斯特式冗長繁瑣且執拗的開始天方夜譚,從梅蘭芳的天籟到莎士比亞早期作品可以信手拈來。文學細胞富足的他很容易得到女孩子的青睞,如何用浪漫發酸的情詩迷惑女孩,說話的語氣怎樣大方端然都運用自如。每當他大談特談時,我不由的嗤之以鼻隨後便會想起廣播上的一句台詞: 最笨的男人才會用情詩去征服女人。
依依是木木的女朋友,學化學的,長相有點像高更畫中的女子,理科生應有的氣質纖毫畢現,身上有時散發着鹽酸和水楊酸淡淡的氣息,長時間呆在實驗室里的身體已經慢慢摻雜了藥物的質地。細長的軀幹總是套着件運動服,依依的眉毛很淡,彎彎的有些扭曲,劉海筆直的像一簇簇流蘇鋪在前額。淡雅的眼神極有穿透力,靜靜的像掃描儀器審視着周圍的一切。愛情的力量是強盛的,墜入其中便不能自己,木木和依依是如此,所有的努力只為換來廝守。華麗的外表往往是偽裝,木木常這樣說。
第一次見到木木和依依也許是一種偶然。看到他倆是在學校附近的一個酒吧。那天是星期一,生意出其的冷淡,天氣也有點讓人避而遠之,冷清而又狹窄的空間僅一幾個人影,昏黃的燈光點綴並襯托出嫵媚曖昧的氣氛,CD機反覆放着莫扎特的二重奏,單調而習以為常。木木和依依在離吧檯不遠的角落坐着,木木嘴角銜着根燃着的煙,手不停地舞動着,好似在玩小孩子自娛的遊戲,依依並未進入狀態,用手托着腦袋冥想些什麼。

曲終人散時已是晚上十一點了,我得趕回宿舍,木木則和依依回到他們的出租屋,據依依描繪無一處是令人歡喜,粗糙廉價的窗簾當陽光斜射時滿是遺漏的光點,幾乎快要坍塌的木質雙人床時常嘎吱作響,衣櫃裡散發着着濃烈的樟木腐爛味道,這些都是依依後來告訴我的。我不能篤定他們幸福的生活着,但是不難看出他們是快樂的、偶爾之間的摩擦是在所難免的,但並不難阻擋他們快樂並無邪的生活。
日子又恢復了以往的平坦,傍晚時分空蕩無人的籃球場上會出現我,木木和依依的身影,鬥牛的遊戲比朝易拉罐里扔煙頭更有挑戰性,籃球智商,技巧的高低是勝敗的直接因素,僥倖的幻想是微乎其微的。木木的戰勝欲望遠勝過他粗糙單一的技術,直到體力散盡,精疲力竭才會罷休,然後躺在地上歇斯底里地大吼幾聲,像是發泄技不如人的挫敗感,依依有時蹲在暗處的一個角落發笑,對木木實在失望時,便像教練似手足舞蹈的指點一番,接着會露出唏噓的哀嘆聲,再後來索性也參與我們的激戰,依依的運動天賦低的可憐,不一會便氣喘吁吁的又蹲到一邊去。
打完籃球後,木木會選一個比較安靜,破落的餐館喝上幾瓶冰鎮啤酒,慰勞一下疲憊的軀殼,這事依依會吵着吃剁椒魚頭,木木表示反對時,他會用化學理論,魚頭的營養價值,科學性天花亂墜的反駁木木無言以對,只能聽之任之。而我則會以自己的最佳方式——沉默來掩飾勝利者的姿態。
依依的例假有幾天沒來了,木木有些慌了。可她卻像沒事似的。
依依,我們玩個遊戲,硬幣呈現正面那麼什麼都不會發生的,就像做過一場噩夢。不幸將會消失。
木木看着手心的硬幣,顫顫巍巍的手有些抖動,好像硬幣在空中翻轉後落下的呈現面能掌控着不幸是否降臨,如影片《老無所依》中那塊決定發生死的幸運幣。木木屏氣凝神的將手中的硬幣緩緩向上拋去,像極了忠誠的信徒在上帝面前祈禱着,然則事實上就是在祈禱,也許,也許太多的原因,包括用力多大,落下時木木的緊張,硬幣在將要出現在木木的手心時忽地落在草地上連續不停的翻轉一股煙的消失在雜草叢中,來不及反應就消遁了,似乎帶在不幸消失了。
上帝耶和華造人的智慧非比尋常,捉弄人的本領同樣非常。
木木的遭遇讓我難免也變的有些緊張,他的束縛,我的自由,無窮的暗涌逼迫我只能在一邊靜靜的扮演自己的角色,天氣變的暖和起來,陽光犀利的灑在每一個角落,依依說,每當這個時候,他們的屋子才有些許的陽光,陽光從窄小,粗糙的窗子小心翼翼的漏進來,家裡便會有了生氣。
六月份了,一切都似乎很協調的進展着,沒有一絲做作。我的生活也無恙的繼續着,某些敏感的東西只能將我摁在一邊去觀望旁邊的是非起落,包括木木,依依。我似乎只是一個無任何思想雜念的旁觀者,純粹的中立者。影的離去,我無法挽回,木木的意外懷孕,我只能目視以待,還有心頭升起的某種與情感不着邊際的撕裂感。
據木木後來談到,那次跟我在山上說過沒多久,便和依依到市區的一個規模比較小,且不是很正規的醫院,早早的就去了,到了下午一個中年婦女模樣的醫生才把他們請到一個類似辦公室的小屋子,簡簡單單的擺設,裡面滿是藥物的濃烈氣味,就像依依經常描述她們的實驗室的難聞氣味,總讓人有種避而遠之的念頭。依依的孩子脾氣總是無形無中在阻礙着事情發展的得當快速與否,不時的抱怨着醫院的拙劣空氣,不時的埋怨等的時間過長,依依的神經質在摧殘着木木心裡防衛的最後極限。
婦女問了些簡單的問題,都是關於前期的症狀,眼神中帶着鄙夷,質疑。好像長期的職業生活已經讓她有了習慣於穿破職業道德的情感自由流露,不屑的眼神聯合着無意的話語讓依依很不耐煩,女人間的對峙是非常可怕的,即便依依還是個孩子,話語中已略帶着刺傷,依依自不是婦女的對手,完全沒有意識到已經敗下。木木在辦公室外呆着,渾身上下在某一部位的抖動牽引着迅速顫抖,不由自己。但是很快便平靜了許多,以前所未有的自控力消磨身上的波動情緒,依依很快就出來了,接着徑直的走了出去。臉上有着難以名狀的苦楚。
回去了才知道,依依受到了婦女的嘲弄,天生的做賤。為了木木犯下的錯而去忍辱負重接受懲罰,一次新生的結束才會換回迷失的錯誤。
大約在臨近放假的最後一個月,木木提出去比較大的醫院。依依覺得馬上就要考試了,等放假了再去處理。木木則說心裡的一個疙瘩早些除去,早些安心。為此兩個人吵了一番,複製了吵鬧中不安和宣洩。執拗,偏執的念頭永遠不會罷休,理智的情緒完全被覆蓋。
兩個人還是去了,一切都順理成章,畢竟是正規的。
下半年,依依搬進了學校,她似乎失去了天真,純潔的秉性,依依也成熟了許多,偶爾相見,臉上沒有一絲的色彩。似乎不幸將她一下子拉扯成矜持的模樣,時刻警備着不幸再次的不期而遇,還是某些痛楚摧殘着她孩子般的心靈,這些東西我不得而知。
快臨近出去實習了,腳步變的緊張,凌亂,沒有過多的時間去消磨,木木也是。只是很少的幾次在酒吧里看到他獨自一個人在喝酒,抽煙,發笑,諸如此類幼稚,深沉的動作,一個男人遭受挫敗的無辜表情。我知道幸福已離他而去,就像小北的消失,他仍在曾經短暫幸福中回味。
作為親近的人,我原本可以去安慰,可以與他一起買醉,可以為他們逝去的幸福尋找轉折的餘地,可以見證某些幸福的片段,可以說些振奮人心的話。
明天,我得坐上火車去遙遠的實習工廠。一個完全未知陌生的地方。
標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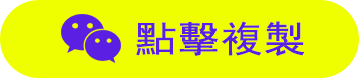




評論列表
有情感誤區能找情感機構有專業的老師指導,心情也好多了
求助
可以幫助複合嗎?
如果發信息不回,怎麼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