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日子就那麼混着。 幹了三四個月,每月也只有兩三千元。坐檯陪酒這一行,沒有底薪,收入主要靠酒水提成和小費。而小費幾乎占了收入的百分之七八十左右。像紅菱那樣的小騷包,酒水提成收入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我還是那樣,一副土的掉渣裝扮,一副唯唯諾諾的樣子,一副略顯羞澀的姿態。了解這一行的人,幾乎都知道,KTV老闆也罷,坐檯女也罷,賺錢主要都靠熟客的。你這個KTV音響好,環境好,位置好,酒水好,服務好,小姐好,人家才肯再次光顧你。而坐檯小姐想多賺錢,首先要你所在的這個場子人氣旺,其次才看你自己拉的熟客多不多。能讓男人舒服,能讓男人揩點油,能讓男人沾點小便宜的小姐,自然收入高。這次你把客人伺候舒服了,下次客人來還會翻你的工作號牌。 在這裡喜歡邊喝酒,邊玩女人的主兒都不是什麼好貨色。但是有諷刺意義的是這類貨色在社會上基本都很有錢,所以只有這一類人肯在這裡大把給小費,而服侍這類人的姐妹收入自然也高。當然,這類人也不會要我這樣一坐下先和客人保持一米距離的姑娘來陪他們。所以我的收入自然不能和紅菱她們相提並論。這個社會的任何階層和利益都是壟斷的,坐檯女也一樣。一個KTV,經常來的肯花錢的熟客也就那麼幾十個人,她們都有自己熟識的妞兒來陪他們。所以紅菱和其他幾個姐妹幾乎壟斷了那家 KTV的高額小費……
1 有一天,姐妹們都出去逛街了。我一個人睡在床上胡思亂想,忽然聽見下鋪隱約有抽噎的聲音。我起身下床,竟然是紅菱在被子裡哭泣。房間裡只有我和她兩個人,我睡在角落的上鋪,估計她沒看見我。不然紅菱是不會輕易在別人面前掉淚的。 紅菱看見我突然從床上跳了下來,有點驚訝,然後轉身朝牆,停止了哭泣,但是身體還在抽噎。我說:「紅菱姐姐,又怎麼了?」我以為是她上次說的發炎的事兒,於是又說:「是不是又不舒服了?」紅菱先是不理我,後來又搖了搖頭。經不住我再三逼問,她才告訴了我原因。 紅菱的家庭屬於城鎮居民,全家沒有一個人有正當職業。當今社會,生活最困難的還不是農民,農民好歹有地種。可是像紅菱這種城鎮零就業家庭連種的地都沒有,在攤上點兒不幸的事情,生計都難以維持。打工沒力氣,做生意沒本錢。紅菱的父親高位截癱,母親下崗,爺爺病的亂七八糟,身體就像個按揭藥店,需要每月投放一定數量的藥品。而家裡唯一的壯勞力,她的弟弟——正在千里之外坐牢,出獄估計在一千年以後。 更糟糕的是她家原來住的地方被拆遷了,現在全家在外租房。房地產開發商拆遷後給她家的租房補貼根本不夠現在的房租。而新開發的房子,按照面積換面積,最小的戶型也比她家原來的房子多出來四五十個平米。這一切也就意味着,紅菱每月必須給家裡支付五六千的費用,來維持她父親的生命、爺爺的藥費和全家的生活,此外她還得再想辦法籌集幾十萬來換一個本來就屬於她們的家。
18

這所有的一切,全壓在我面前這個蜷縮在被子裡痛哭的女人身上,是的,她叫紅菱。以風騷和奔放聞名的紅菱,以搔首弄姿拼命賺錢著稱的紅菱,任何男人掏一百塊就可以拔她私處一根毛的紅菱!她月收入最低七八千,好的時候也過萬,她為了賺錢得了婦科病,她為了賺錢經常喝的七葷八素。
紅菱一邊說,一邊哭,最後我和她擁抱着一起哭。我們當時哭的很厲害,幾乎可以用嚎叫來形容!起初我傷感是因為她的不幸,可是哭到後來,我也不知道是因為自己的辛酸還是她的艱辛,就那樣,整個房間只有哭聲……那唯一的聲音,單純而悽慘,純真而悠遠,直達心扉,深深地刺痛了我!
1
記得那一個月,我從牙縫裡擠了三百塊錢給紅菱。可是她說什麼都不要,紅菱對我說:「我有錢,卡上還有兩三萬。可是不敢花,怕哪天突然就沒工作,沒飯吃了。」紅菱的這種心情我很了解。干我們這行,這個月有兩萬塊的收入,但是下個月可能就一分都沒有。對未來的未知和恐慌,永遠在心裡蔓延,我們根本沒有安全感,手裡有錢,但是很怕,很怕明天就沒有了收入,吃什麼?喝什麼?這其實是窮怕了的表現。
我又給紅菱給過兩次錢,她都執意不要。她說:「好妹妹,你更需要錢,姐姐有。」看她很堅持,我也只好作罷。當時覺得和她相比,我幸福多了。除了一堆外債,我還有個完整而幸福的家,雖然只是幾件土木結構的破瓦房,但那是屬於自己的。而她呢?
從那以後,紅菱更是拼命地賺錢。而我還是那樣,業績提成始終保持在倒數第一二位,成績很穩定。
有段時間,紅菱請了幾天假,什麼都不干,就躺在員工房休息。我問她怎麼了?是不是有事?她偷偷告訴我:「我去隆胸了,經常有客人嘲笑她胸小,不給小費。」
我低頭看了看,果然有變化。她說得休息一周不能有劇烈運動,兩周以後逐步拆線,一個月以後才基本正常。
紅菱大概休息了二十天左右,又開始工作了。而我在月底的時候則被業務主管叫去談話。業務主管是管酒水銷售這方面的小頭目,從某種意義上說,也就是麗姐的上司。他把我叫到辦公室說:「小靜啊,你來快半年了,銷售怎麼還這麼低?凡是你的包房,酒水消費都比其他員工低三四成,我給麗姐打過幾次招呼,她總是說你是新人,要我多擔待。你要我擔待到什麼時候?」
我低着頭不說話,心裡清楚,麗姐沒告訴我是怕我為難。只有漲紅了臉保持沉默。最後業務主管攤派了:「再給你兩個月機會。」意思很清楚,兩個月之內沒有起色就走人。
回到員工房我大哭了一場,麗姐、紅菱、少華和其他姐妹都來安慰我。我很怕,我怕他們把我掃地出門,我去幹什麼?
一切還是那麼迷茫、那麼無助、那麼艱難。出去找事做,一個月也就1000多元的薪水,還要另外掏房租,除去房租和其他開銷,每月最多往家裡寄兩三百塊錢,那能起什麼作用?一個多產的母豬,一年的貢獻都不止兩三千吧?我當時很恐慌,不知道我的未來在哪裡,這樣下去怎麼辦?
最後,麗姐和紅菱安慰我說,一定會照顧我。我才勉強平復了情緒。第二天,少華幫我買了幾件衣服,都是很性感的那一種,大網洞褲襪、超短裙、豹紋圍胸、黑色連衣裙、透視裝等等。此後,紅菱的熟客來了,如果需要兩個以上的姑娘,紅菱一定會叫我過去作陪。
20
雖然不情願,但是也只有改變風格,換上了那種衣服。剛開始穿上的時候,渾身不自在。過了一段時間,或許周圍的人都那麼穿吧,漸漸地也習慣了。
第一次和紅菱一起陪酒,客人是幾個生意人,聽他們言談貌似是做服裝的。在包房裡,他們拉這紅菱跳貼身舞,而紅菱看上去也很開心,隔着薄薄的襯衣在客人身上蹭來蹭去,我很看不慣。一會兒其中一個客人來拉我的手,我本能地掙扎了一下,坐在對面的紅菱給了我一個眼神,我耳畔也仿佛想起了業務主管的那番話,慢慢地我閉着眼睛把手放在了客人手心裡,給他端了一杯酒。我記得很清楚,那個客人喝完酒後,手在我胸前游離,然後摸着我的脊背說:「你這身材穿上我們夏季新款女裝最合適了。」
我含着眼淚,默默忍受着一切,而紅菱則在暗暗拍了拍我,示意我挺住。好在包房裡燈光比較昏暗,客人沒有發覺。紅菱對這些男人卻應付地輕車熟路,客人不但摸了她的胸,幫她介紹了一款所謂的新款胸罩,而且她主動請客人丈量了一下她內褲的尺碼。
最後,客人走的時候我得到了兩百塊小費,紅菱拿到了四百塊。做過夜場的都知道,通常情況下,一晚上只能做一單。因為客人都是黃金時段來,到凌晨才走,根本輪不到第二輪。所以我那天的收入也就是兩百。按照這樣算,我這個月可以拿到五六千左右,幾乎是原來的兩倍。
那晚我手裡攥着兩百塊錢,又默默地流淚流了一夜……
2
後來我經常和紅菱一起坐檯,有她的包房肯定有我,有我的包房裡肯定也有她。我也學會了高山流水等喝酒的絕技,高山流水就是右手四個指縫各夾一隻口杯,然後90度彎曲,右手大拇指朝胸口,逐漸抬起右手,嘴唇搭在大拇指和食指之間的口杯上,小拇指慢慢抬起,讓最高處的酒杯里的酒逐一流到下一個口杯里,最後統統流經你嘴邊的這個口杯,一次喝四杯酒。紅菱告訴我,這樣喝酒最快,喝的時候手適當發抖,讓酒灑出去,這樣酒消耗的快,我們也喝的少。
慢慢地,我也有了喜歡我的客人,也有了我的熟客,有很多客人來都直接翻我的工作號牌。業務主管再也沒有為難過我,但是我的收入比起紅菱還是望塵莫及……
轉變風格後的第一個月,我給家裡寄了將近4000塊,或許是3000塊,具體多少忘了,畢竟隔了太久。但是我至今記得很清楚,媽媽高興地打來電話,聲音很輕快,她很高興地說:「閨女啊,家裡有希望了,大家都很高興,我閨女出息了。」我聽了也很高興,自從有了龐大的外債,一家人總是悶悶不樂的。沒有過這種沉重負擔的人或許無法理解這種無形的壓抑,在別人眼中或許很小的一筆錢,甚至是有錢人的一頓飯錢,在我這樣的家庭中卻是無法解決的困難、足以令人窒息的壓力、足夠讓我改變一生的負擔。
2
接電話的時候,我和媽媽都很高興。可是掛了電話,我心裡在默默地流淚……這種小幸福,或許連幸福都算不上,只是對未來有了朦朧的希望,這種感覺對我們家來說,真是來之不易。
那天,我破天荒地請麗姐、少華、紅菱還有珠兒吃了火鍋,平時她們幾個最照顧我了。當時我只是覺得紅菱和我一起坐檯是照顧我,可是後來我才知道,還有其他原因。
之後的兩個月,我的月收入也在6000元上下,很穩定。慢慢的我肩膀上的負擔逐漸輕了,再沒有了侷促和不安。時而蔓延自心底的恐慌和迷茫還是無法散去,我不知道如何從根源上消除這些。
日子還是這麼過着。
轉眼到了春節前夕,有些姐妹已經動身回家過年了。越早回家過年的姐妹,一般都是壓力負擔越輕的姐妹,平時只陪酒,不出台。遲遲不肯回家的姐妹,多是經濟壓力比較大,或者是出台的那種看淡人情冷暖,對家沒有眷戀的姐妹。
我本來也打算回去的,紅菱卻對我說:「現在臨近春節了,生意火爆異常,而且姐妹也少了,回家幹什麼?抓緊賺錢啊!」
我看着卡上的那兩三千元,除去來回車費,所剩無幾,想想也對,就留了下來。
春節前夕,生意果然異常地火爆,就連平時空閒的午檔時間都經常有客人。我有時候自己去包房,大部分時間都和紅菱在一起。
23一天中午,包房有人找姑娘,姐妹們都還在睡覺。我就過去了,只有一個客人,對我也沒挑剔。這傢伙要了一桌子酒,邊唱歌,邊喝酒。他唱完一曲溫兆倫的《你把我的女人帶走》後,轉身問我:「你叫什麼名字。」我說:「小靜。」
他喝了一杯酒說:「小靜?呵呵,你自己隨意喝吧。我們倆都隨意。」換了半年前的我,估計也就不做聲了。可最近兩三個月來,我膽子大了很多,於是對他說:「一起喝嘛,你一個人喝什麼酒。」他擺擺手說:「隨意喝吧,我酒量一般。
說完他又開始唱歌,不再理我。」
接連聽了他唱完《再回首》、《東方之珠》和一首忘了名字的歌后,我忍不住了。對他說:「一起喝吧,你一個大老爺們兒一個人喝什麼悶酒啊。我給你表演個高山流水吧。」
說完我夾起四杯酒一飲而盡。他楞了許久才說:「隨量吧,我叫個人來只是想聽我唱歌,陪陪我,我怕寂寞。」
聽了這話,我總感覺怪怪的,我還從未遇見過這樣的客人。看着他自己一邊唱一邊喝,我覺得挺無聊的。過了一會兒他略微有了一些醉意,我數數桌上的瓶子,他才喝了五、六瓶而已,看來酒量真是一般。
唱完一首《孤枕難眠》後,他不停地喝酒,兩三瓶下肚,他竟然哭出了聲音。我有點手足無措了,這麼窩囊的男人我還是第一次見,我也懶得理。他突然自言自語地說,出來四年了,沒回過家,老婆跟人跑了,兒子估計都不認識他了,那個家還有什麼意思……
他突然拿出一百塊給我說:「走吧走吧,滾出去,我要靜一靜。」我看他跟發瘋似的,自己就拿錢出來了。這是我掙的最輕鬆的消費,類似這種怪人,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有一個。
曾經有人喝醉了以後拿出一疊錢來全場派發,也有很摳門兒的,喝酒前給姑娘小費,喝醉後又要回去,總是千奇百怪什麼都有。
24
慢慢地我也總結出規律了,最賺錢的包房是請當官兒的辦事的房間,姑娘進去後只要能把主客哄開心,請客辦事的老闆會大把大把地給你錢,我一個姐妹在這樣的房間裡一次就拿到了小費2000元。其次是談生意的包房,遇見老闆談判順利,心情好的,也有大額紅包派發。最窮酸的就是什麼同事聚會房啊,生日房啊等等,一般最多也就100塊。
我那段時間就那麼不痛不癢地混着,收入也比平時高了很多,偶爾會想想家,有一種落寞的孤獨,但是想想家裡那一貧如洗的情況,又會拼命去賺錢。
有一次跟紅菱去一個包房,進去後一群看上去像黑社會的男人就如饑似渴地到處摸,紅菱倒無所謂,我卻渾身不自在。聽客人們聊的隻言片語,這群人好像是去哪裡賭博,贏了一些錢,都很開心,而且出手比較大方,1888元的紅酒就要了兩瓶。
他們有五六個人,一個人唱歌,其他人喝酒。其中摟着紅菱的那個黑西服最為流氓,牙齒叼着紅菱的衣領往下扯。抱着我的這個小個子雖然比黑西服老實點兒,但也不是什麼好貨色。右手中指不停地在我屁股中間來回搓,我只好時不時地把他的手挪開,我藉口起身去洗手間,才逃脫他的鹹魚手。
我在廁所離躲了大概半小時才出去,出門一看,包房大廳里一群人,黑西服和小個子們每人拿了一杯酒圍在中間。紅菱蹲在圈子中間,張大嘴仰視着周圍的這五六個人,他們則輪流拿了一杯酒,高高地、緩緩地忘紅菱嘴裡倒,紅菱用嘴在下面接了酒直接喉嚨一動就咽了下去。一群男人一個接一個往紅菱嘴裡倒酒,倒完一杯酒往紅菱手裡塞一百塊錢。我實在忍不住了,走到黑西服身邊說:「大哥,要不給你們找幾個肯出台的妹妹玩吧?」沒想打黑西服大笑着說:「好啊,好啊,快找來!說着塞了我兩百塊錢」
我出門找了幾個出台的姐妹進來,黑西服們每人選了一個在這些姐妹身上摸了摸就帶走了,當時的場景跟挑牲口沒什麼分別!
標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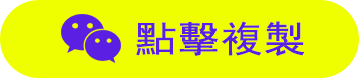




評論列表
兩個人的感情往往都是當局者迷,找人開導一下就豁然開朗了
求助
可以幫助複合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