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逃離
結婚10個月零24天,凱就心平氣和地和我商量離婚的事了,仿佛我們之間從來與愛情無關。強烈的自尊驅使着我的倔強,點頭,好啊。
看他眼裡掠過一絲訝異,我心裡冷冷地得意。當濃濃的煙味被一個關門屏蔽在書房內時,我突然把不到自己如珠連滾的脈象了。
第二天一起上醫院,他簽字,我住院。

三天後,我腹內六個月的什麼結晶就在高科技手段下被製造為醫院的垃圾。從針水起作用到陣痛到分娩再到移床,整個過程只是痛,身體和靈魂都在爭搶着做隱忍的首席。
一周後,凱去了F省,我則在親友疼惜的目光中坐上了到I國的班機。
陌路,原來如此簡單。
(二)煉獄
簡直就是煉獄!住在悶熱潮濕的出租房裡,我不禁抱怨剛死於車禍的朋友。
才到I國第二個月,那個「花言巧語」騙我過來投奔的好友就被超重飛卡送進了天堂。
他父母早逝,又沒結婚,真是去得了無牽掛。只是苦了我。剛磕磕絆絆地學會從一數到一百,蹩着那講一二十遍本地人才做恍悟狀的問候語,我租下附近的一間小屋,開始了隱姓埋名的離婚療程。
夜夜枕着淚水和回憶,在黏汗的濕熱中無眠。這是個熱帶國家,蚊蟻成群來與我為伴,絲毫不管有沒有老感情,親熱地不是吸血就是啃肉。原來不是熟了才親近,也不是疏了才遠離。
臥着涼蓆,我點了一支本地煙——生平第一支煙,想起一句話,「我把你的名字寫在煙上,吸進肺里,離我心臟最近的地方。」可當我把凱的名字吸進去時,肺只顧着猛烈的以咳嗽來頻震,他的名字早已碎得忘了親近心房。什麼地方啊,煙都那麼劣。我皺眉,起身弄息了煙頭,順便按死幾隻正在覓食的螞蟻。
由於產後沒有好好休息,又處於極度悲痛和絕望中,我常常發燒怕冷。舌苔白得像塗了厚厚的石灰,手心毫無血色卻時時處於高溫狀態,就像練了火砂掌,只是心跳得振顫,無論坐躺,滿世界都在我眼前有節奏地雀躍。各處動脈在皮下不安分地跳着,看着手腕手心和指縫隨心臟有規律澎湃着思念,才發現很多東西藏得那麼膚淺。可把脈時,只覺細弱微急,不似那麼洶湧,原來眼睛看到的也不一定就是真的,就像我對離婚的默然。
大多時候以回憶為食,關了門,竟自躺着,分不清晝夜,昏昏沉沉地任胃痛伴着思憶時而清醒時而迷糊。三四天泡包方便麵來延續生命。感覺靈魂隨着肉體在縮水,離散。夢魘的頻率大大增加,還有好多次都在恍惚中看見自己靈魂自肉體飄出。我靜靜地在等待中活着,感受行路時似乎離地三尺的御風飄移。死神偶爾對我笑笑,並不說話。遺棄我的,不只人間,還有冥界。粗糙的舌舔着乾裂的唇,對鏡子笑了。我要喝水。就在起身的瞬間,世界一片黑暗,腦子裡轟的一聲就什麼都不知道了。
睜眼時,夜如我杯里殘留的咖啡般濃稠,滲入眼裡,苦進心裡。開門,吸口月光,轉身瞥見鏡子裡一條細細的線在臉上怪異地笑,拉燈,撫着左頰自憐。心痛還是傷痛?似乎一時都麻木了。蚊子,只有這些嗜血的生物還在夜裡愉快地嗡嚶。
又躺了好多天沒出門,突然在一個早晨,聽到有人喚我的名字,吵吵嚷嚷,由遠及近,然後看到凱歸來的身影,還沒來得及高興,就被驚天動地的擂門聲吵醒了,開門,是很多訝異的眼,房東看到我後點頭笑着致意,嘴裡嘰里咕嚕着我聽不懂的東東,然後和鄰里們一起消失了。呵,擔心什麼呢?我還活着。抬頭,晨光刺來,深深、深深的痛。
關上門,想到了死亡的問題。關於自殺。首先是割腕,記得初中時有個女同學割腕自盡未遂,返校後給我看她縫了五針的左手手腕,說,好痛啊。我一時皮麻骨酥,不行不行,對自己下不了手。接着想到吃藥,可是這裡人生地不熟的,難,再說如果發現被搶救要受灌洗之酷刑,不妥不妥。然後呢?上吊,聽說很痛苦,到時舌頭在繩子作用下還會伸出好長,不雅不雅。還有什麼?跳樓,哎,摔死了倒好,摔不死落個殘廢就慘了,再說跳樓這個工作我一直認為是作秀,死得有自我炒作之嫌,如同臥軌和撞車,太曝光了,不合我低調的性格,三者都被否了。投河吧,雖然一直想着死後骨灰要撒到海里去,可那是飛灰的事,要以肉身代之還是不大敢行,一是旱鴨子的我嘗過幾次水裡自由落體亂撲被嗆的難受,二是沉下去總要浮起來,浮起來的形象,哎,太不體面了。其他呢,還有……
頭要炸的時候,我就停止了所有關於死的假設和推論。既然都要推翻,為何要假設呢?既然沒有結果,為何要推論呢?結婚是假設嗎?可是被離婚推翻了。離婚是結果嗎?為何結婚時沒有推論出?
第二天,我起來收拾房間,洗東西,打掃衛生,然後在鄰舍的議論聲中出門採購了。
末了還買些書回來,既然不想回國,也懶得換地方,就姑且着適應吧。
(三)孤痛
漸漸地開始半通不通地和周圍人簡單交流了。認識我那位故友的人偶爾和我說說他生前的事,說他在這裡原來有個女朋友,同居了很長時間,後來不知怎麼消失了;又說起他的工作,似乎境況不大好,我也聽不出個一二,反正他死之前,對我挺大方的,雖然他這人喜歡充胖子,但良心挺好,否則我也不會過來。哎,怎麼就去了呢?
我住的地方在學校附近,一大片都是出租屋,這裡的學校很奇怪,沒有宿舍,學生都自己在外租房。雖然很多高校集中在這裡,但已屬於郊外了,離城很遠,本地人都是巧克力膚色,還喜歡穿暗色的服裝,皮膚配上着裝整個色調都是昏黑,似乎裹着不可告人的哀愁。
在朋友介紹下,我開始給兩家華人的子女補習漢語,一周四次,每次兩小時,倒也輕鬆,報酬也不錯。
9月以後,常常會看到很多白種人的面孔,據說是藝術學校的政府交換生。到11月時,離我住處不遠的地方開了一家咖啡店,第一次看到時感覺很突兀,貧窮落後的穆斯林鄉村里,突然有一隅散發着濃濃的典雅和時尚,新鮮的氣息。想來是為了賺那些又吸煙又喝咖啡的外國人銀子而建的吧。
一周後,我也坐到了這間鄉村咖啡屋的一角,這裡都是外國人,不說本地話也不說英語,反正每張桌子一個世界,而我的世界裡只有我一人而已。燈光很昏暗,但不是情調的關係,而是這裡供電不足,每家用的燈泡都劣質到了極點。我有時看看書眼睛就生疼,只是在這裡,好像很合調調。原來使用價值也是因時因地而異的。那愛情呢?如果我的愛情用在凱身上就像用來看書的燈光一般不堪,那麼哪裡才是我愛情的咖啡屋?在哪裡我的愛情才有情調?
和服務員要了一支煙,這裡的煙都是零賣,飯館裡也是一樣。澀澀的煙味混着苦苦的咖啡,進到胃裡是一種很奇怪的感覺,就像那塊桌布的抽象藝術一樣,讓我的痛楚也異化了。其實,我更需要一點酒精。咖啡讓我更清醒得記得和凱在我們的小窩裡煮咖啡的溫馨,是的,我該要點酒來沉睡。
回到房間,咖啡激起的興奮讓人無法入睡,回憶起凱的唇,濕濕的溫熱似乎還在向空氣里散着氤氳,柔情未盡心已寒。真的有過曾經嗎?煙圈只顧着妖舞,不回話。他也在吸煙吧?我若是他手中此時的煙,該多幸福……一瞬間,又恨起自己的卑微來,愛情,讓靈魂降格!我瘋狂甩頭,散發凌亂了一身,打掉了煙頭的赤紅,看着幾根發着焦臭味的髮絲在痛苦中扭曲收縮,我感覺自己吃了搖頭丸。心臟突然跳得厲害,我的手捏着那隻滅了的煙在空中抽搐着曲線,劃出一圈一圈的絕望,繼而全身都開始機械震動。
我以為要死了,死在五杯黑咖啡里。顫抖着摸過手機,好想給凱短信,可是我根本連按鍵的能力都沒有。躺倒,半小時後,死神就懶得和我開玩笑了。我狠狠狠狠地埋怨了命運一夜。
直到晨光從門縫窺探到手上的結婚戒指時,我才開始有了朦朧的感覺。於是昏睡。
(四)過客
第二次到鄉村咖啡屋時,已經是一個多月後了。
人不多,可能時間早的關係,只有兩張桌子坐了人,靠門的那張是兩個高挑白皙女人,一個妖艷一個清麗,都很養眼,我不經多看了幾秒,並對比着她們的美,猜想她們的性格。很喜歡欣賞身邊的美,沒有階級,沒有年齡,沒有性別,沒有任何界限,不只人,還有大自然的一切。
似乎被我盯得不自然了,她們借着吐煙圈瞬間,彈着煙灰,往我這邊看看,然後繼續若無其事地聊天。我冷然地掠過她們的臉,把目光投向另一張桌子,手裡把玩着桌上的小魔方,似乎剛才對她們的目光賞玩也和手裡的把弄一樣不經意。
這間吧本也不大,一共就8張桌子,大概因為下雨的緣故,感覺今夜咖啡的醇香中有一莫名的潮濕,一種冷寂在空中流動。當我的指尖觸碰到滾燙的杯身時,身體不由打了個寒顫。
Hello!定神時,一隻手在我面前,指尖微微上翹,柔軟,纖長。抬頭,是男孩一雙友好的眼睛,不是本地人的樣子,不知道什麼時候進來的,大概我聽音樂聽得入迷了。伸出手,我也禮節性的打聲招呼。可以坐這嗎?當然。我大度的笑笑。
是個泰國人,滿口泰式英語,胡亂應了幾句我就不想搭理了,問題多得煩人,我討厭別人總問我問題,這讓我更加想念凱的內斂和深沉。他說在附近見過我幾次,總是低着頭,行色匆匆的樣子。我笑笑,「是嗎?」他說,「你笑起來的樣子很甜,為何常皺眉?女孩子多笑笑會更美麗。」我用眼睛擠個笑容給他,哦。
末了,交換手機號,他執意幫我付帳,說是很高興認識我。我也懶得客氣,隨他,一個謝字笑過去,認識你我也很高興。話音未落我就在掂量自己話中有幾分真誠,看看他的眼睛,很高興的神情。我嘆口氣,心裡說:小孩子。
再後來,他一兩個星期發一條信,似乎像我突然發神經記起某個人一樣地冒出來。
最後,他就消失了,放佛從來沒出現過,沒有感情的東西當然不需要維繫。
(五)放鬆
此前一個多月,我又去咖啡屋,偶然就認識了一對華人兄妹,妹妹漢語很好,哥哥能說一點但不識字。初次見面相談甚歡,他們都會放聲大笑,那笑聲的光波可以震撼陰陽兩界——我當時就那麼想的。由於是華人且爽朗,兩個多小時的座談我們就成了好朋友。
此後這個34歲了還像個小孩子的哥哥F開始對我發起猛攻,每天都要開車來接我出去吃飯或遊玩。遇到我作家教時,就送我到學生家,末了再接我回來。他常常給我買小點心,買小首飾,買小精品,還買書買碟,他在我身上大筆大筆的揮霍着仿佛不是錢的錢。
我們去城裡的慢搖吧喝酒,去格調很高的咖啡屋聽音樂,去星級中餐館用餐。我們在山頂眺望,我大呼着凱的名字,響徹山谷,卻越不過峰巒。F笑着看我,你喊什麼?我說沒有意義只是幫助出聲,以此表達內心的高興。我喜歡站在山頂對着世界呼嘯,仿佛那匹孤獨的野狼就是我。我們在海邊逐浪,我在白白的沙灘上一遍又一遍寫着凱的名字,寫着我刻骨的愛情,浪一層又一層地湧來退去,帶走了我的文字,卻帶不走我的思念。F笑着問我,寫什麼呢?我說這是一首詩,一個偉大的詩人寫的。他看着「詩」搖頭。我放聲大笑,餘音在海面盪啊盪啊,一個浪來,濕濕的回音冷透了心扉。
油價上漲時,我的房租也漲了。出租房還總是停電,在F妹妹的熱烈邀請下我就暫時搬進了他們家。出租房沒退,任它空着,我想等厭倦了我就回來。我知道什麼都有時限。
生活還是一樣的無聊,我們早上去吃早點,然後隨處走走。呆房間裡就看碟,這裡有很多很多華語武俠片,新的老的,一應俱全,看完了再租再租,天昏地暗。
房間很空曠,也屬於本地人那種不見天日式的建築風格,24小時都得開着燈。但已經比我那出租窩好千萬倍了,儘管和國內比起來不盡人意,不過可以洗熱水澡,有空調,每天都有女傭為我服務,我很容易滿足的,雖然心靈空虛。
回神處總是充滿了對F兄妹的厭倦,說不出來,無論他們對我多好,我依然品不出一絲人情味,曾經的一切讓我在現實的落差下無可容身。
三周後F的妹妹就總很少出現了,問就說她母親叫她留那邊家裡有事。於是只有F過來陪我。一開始我們看完碟就睡兩個房間,再後來看至凌晨甚至通宵就躺一個床上了,用一個長長的抱枕隔在中間。F總吵着熱啊熱啊,雖然空調只有16度。我背着他自顧自地睡,很多時候眼淚靜靜地流,把我的夢流的濕濕的。
有一天F突然租來了《色戒》,我說我們兩個看不合適吧,他說怕什麼又不是小孩子。我笑笑,OK。那天晚上,我看得毫無感覺,他卻一會兒下床去走幾步,一會兒去樓下拿瓶冰水,連道好熱好熱。放到很暴露的場面時,他就假裝去衛生間。我心裡笑,呵,誰是小孩也不知道。
(六)出軌
一周後的一夜,當F從我身上下來時,不停地用生硬的華語道歉「對不起,對不起!我也不知道會這樣。對不起……」
我冷冷地用鼻子笑笑,沒關係,我累了,睡吧。繼而轉個身,不理他的尷尬與窘樣。
也不知道是怎麼開始的,剛才看着個幽默片高興得忘乎所以,中間的「三八」抱枕不知甩到哪裡去了,接着他撓了我身上一下,我本敏感,在床上咯咯滾做一團,他來勁了,不停撓我,我在自衛的空隙里也還擊着他,再不久後擾癢變成撫摸,大笑變為粗喘,再然後,我的睡裙被掀起,他就這麼進去了……
整個過程,F顯得拘謹而慌張,柔弱得無力。我一邊想着凱,一邊冷冷地看着在我身上笨拙用勁的他,大腦一片空白,沒有拒絕。最後,F說這是他第一次。此後很多很多時候,他都會說,那是我第一次啊,我撇撇嘴:「別說叫我負責!」他就像個孩子似的,「要你負責,你得對我負責。」每每這時,我微笑看着他,心裡有種欲嘔的衝動。
F說在我之前他只愛過一個女孩,那是18年前他16歲的事了,那個女孩後來去了美國,他本也想跟着去,母親不允許,只把他送到中國廣州去呆了兩年。那女孩一直沒回來,他說他一直在等她,直到三年前聽說她已經在美國結了婚,才發現早已沒有了初時的感覺。
我說,「我不要再結婚,一輩子一次就夠了。你年紀也不小了,好好找個女孩娶來做妻子,好好過日子。」「我會改變你的,我會努力,我只要你作我的妻。」他很自信的樣子。 「可我只愛凱一個人」,「慢慢就不愛了。愛情可以經營,就像也可以忘卻一般。」我搖頭,「你真是個天真的孩子。」接着就是靜默,時鐘在牆上滴答滴答,空調兀自吹着。突然好想哭,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這樣。
F的父母對我很好,雖然他母親是個厲害的角色,我有時有點怕她。每次吃大餐她都要叫上我,每次逛超市,都拉着我的手不停和我說這說那,她的華語比一雙兒女都要好。她常常會打聽我的家庭情況,打聽我將來的打算,偶爾會問些禮數問題,再有意無意說些個婆媳之間的事和她的觀點,再說些媳婦應盡的責任,仿佛在讓我寬心,讓我知道她會是個很好的婆婆,也似乎是在教導我這個她認定的「未來媳婦」,每每這時我就特別注意回話,生怕不小心就讓她誤解。
我常和F說,你這麼大年紀整天什麼都不做,只知道吃喝玩樂,不好吧?再後來,有時和他母親談話時也有意無意地提起男人的事業問題,然後她母親就張羅着給他找合適工作了,他們是商人出身,F說對電腦感興趣,於是租了房,設計好宣傳單和鋪面,他母親讓我陪他到首都去進貨,交代我把每天的消費記在本子上,回來給她看,還有進貨的金額。我聽了就頭暈,一直想着怎麼才能推脫。管賬?我最頭痛的事了。我的本意是等他工作了就忙了,我就有藉口說不好打擾然後搬回去,沒想到幾乎把自己攪進去。幸而那時首都機場鬧水災,就拖了個把月。
(七)掙脫
我越來越冷了,有時莫名地對F發火。看得出來,他真的很努力很努力的包容我,也在物質和感情上盡力滿足我;其實,我也在暗中努力過,可是慢慢發現的是,我連和他作朋友的興致都被朝夕相處的乏味磨滅了蹤影。我在想為什麼和凱談了6年戀愛,又結婚快一年,我卻還沒厭倦呢?這是愛和不愛的區別嗎?
F的母親一次又一次提起F年紀大了,他父親也70了,都希望他早點成婚好抱孫子,然後就用那刀鋒一樣凌厲的眼神挖掘我眼中的信息,我鎮定地說,男孩子嘛,不急的,不急的。心裡卻在尋思,真的得逃了,要再呆下去,時間越久可是越難抽身,還給老人以為我真想嫁她那飯來張口衣來伸手,什麼都不會的寶貝兒子呢。
五個月後,我毅然搬回了那間昏暗依舊的出租屋。理由是F要工作了,我不想再麻煩他總是接送我去學生家裡,他母親說不麻煩不麻煩,可以讓司機送的。我笑着搖頭,「謝謝阿姨了,我還是回去比較方便一點。」看到自己眼裡映出對面一種極力掩藏的憤怒,我趕緊轉頭顧他。她肯定說我不識好歹,那神情就像到口的肥肉飛了一般,還有種惱羞成怒的味道。我就只有一個信念,逃!
收好行李出門時,我看到F受傷的眼,他一聲一聲地嘆息着,「哎,我的詩詩要走了,嗚,我的詩詩要離開我了……」我轉身白他一眼,「大男人整天哼哼唧唧,像什麼話?誰是你的?!我只屬於我自己!」話音一落,又有點心疼這個給了我第一次的男人。心裡不禁黯然,凱,我始終沒能把愛情成功轉移過去。
我曾經也是真的想過在這個陌生的國度找個人打發後半生的,F開始追我時,我也想過是否就依了,他是真的愛我的,雖然,我有時簡直感覺這個富家公子像個白痴般的叫我無奈,他單純到連愛都不知怎麼愛。我可以不在乎他走路的姿勢有多難看,可以不在乎他相撲一般的身材。可他要是多那麼一點點成熟,不是像個小孩子整天撐着個腦袋哼哼唧唧惹人注意,即使晚上他還是一直夾抱個枕頭睡覺再把其中一個枕角放進口中做吮吸狀也無所謂。要是上街時幫我拎拎包,而不是自顧自的昂首挺胸一路向前;要是吃飯時為我夾夾菜,而不是把所有喜歡的都攬到自己面前,取了也不懂得在推回原位,只顧吧嗒吧嗒的自己吃,讓所有盤子都以他為中心呈半月環繞,其他人面前兀自空了一大片;要是他坐下來時,可以不像本地人一樣用手摸玩腳掌,可以洗手後再往嘴裡送東西,可以像其他華人一樣懂點衛生規矩和禮貌;要是他不會換褲子時讓褲子如望遠鏡般睡在他雙腳跨出的原地;要是他可以不在公共場合說話和爆笑如雷;要是他可以……也許我會。
(七)孤獨
搬回來後,我就總回絕着F兄妹的邀約,推說身體不適,或是有課。F一直堅持着,短信,電話,偶爾帶堆食物過來,我總是冷面相對,一句淡淡地謝謝,就閉了口。他漸漸地發現了自討沒趣的卑微,肯定還狠狠在心裡說我不識好人心,從他又愛又恨的眼神里我就看得出。我討厭他的眼睛,那種諂媚的眼神醜陋無比,笑起來都不美。我才不理他那故意表現的可憐狀,反正我不在乎,再說我也從來沒承諾過什麼,不必要內疚的。我甚至驕傲地想,我離開是我仁慈,不希望他再淪陷,也好清醒的面對現實,好好尋個女孩結婚生子,過正常人的生活。我可是有過婚姻史,不知怎麼應付他那厲害異常的母親,我可不想過那種似乎低人一等的生活。
再者,F是懦弱的,我從不同情懦弱的人,對於他們,我只有鄙夷。他沒有主見,比我還孩子氣,除了可以為我揮霍金錢,他一無是處,更何況文化差異如斯。如果是朋友,我大概可以忍受,但,決不可能是我能承認的男朋友,更別談丈夫。他沒有自由,一切都在母親或妹妹監控下,包括用錢,他身上只帶卡,就如她妹妹身上只帶錢一般,我討厭他每次出門前都和妹妹要錢。反正我已經找不到不讓我挑剔的一絲一毫了,我有時甚至感覺噁心,居然和他發生過關係。
回到出租屋,生活依舊,思念的空間更多了,凱越來越多的出現在我夢裡夢外,沒有課的夜裡,我都在咖啡屋呆着,偶爾和一兩個那人漫不經心地搭訕,說些沒有靈魂的話,出了門,誰也不認識誰。我越來越懶了,我想把自己包裹起來,可是又渴望呼吸新鮮空氣。
父母總是在電話那頭呼喚我,回來吧,我們好想你。你過得好嗎?要不要錢?不好在就回來吧,啊。每每這時,我就潸然淚下,想到父母日漸衰老的容顏,我卻躲在天涯這邊為了那段莫名其妙的婚姻過着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我到底怎麼了?
恨自己恨到要發瘋時,我就在夜裡用刀片沾着月光在手臂上劃啊劃,每一條紅線都一般長短粗細,像素描里的排線,從腕到肘,密密整齊的排列着,紅紅的,看進心裡又癢又痛,如思念,撓了就痛,不撓又癢,真是劇毒無比。聽說破傷風會死人的,說是傷口見了鏽就可能感染,不及時治療就會要了命。我換了片有點鏽斑的試試,腦子裡想着死在異鄉是個什麼情景。必然先是被嗜血如命的螞蟻觀光,之後白骨被人發現,等到父母知道時肯定已是個把月了。父母,想到父母時,我加了些力道,划過後,再用手一擠刀口,粗粗的紅線上斷斷續續冒出些紅色的小珠子,血色有點暗,大概缺氧了,我想。活着吧,父母沒錯,別傷害他們,我對自己說。於是再次狠狠地擠了擠那道深深的血口,讓可能進去的鏽隨着血流出來,與破傷風絕緣。
此後的夢裡,除了凱外,也多了父母的身影,還有爺爺奶奶外公外婆,遠近親疏的親戚們,我想我開始想家了,孤獨感在疼痛中漸漸清醒了。可想到回家,我還是對自己搖頭,再等等吧。傷口還沒愈呢。
(八)學生
一個人在久了就會寂寞,更何況是個結過婚還生過孩子的女人。當身體漸漸恢復時,我發現自己有了肉體的欲望,那種人性的本能讓我焦灼。
雨季不知不覺又來了,可是沒有一絲涼意,這個鬼地方,下雨都能保持30度。我煩躁地在昏暗的房間裡踱步。望望慘澹淡的天和如注的雨,一支接一支的吸煙。日子在方便麵的膨脹和咖啡的濃稠中流逝。刀片還是歸肉體,思念還是歸靈魂。
一個周六早上接到個電話,是原來和兩兄妹去歌廳唱歌時認識的一個華人小伙子D,說是從F妹妹那問到了我的電話,有人想找我補漢語,方便就見個面,於是約好當天5點來住處接我。記得D皮膚很白,身板不錯,很陽光,漢語口語也不錯。當時我和F妹妹開玩笑說,這小伙子不錯啊,怎麼不試試?她說,天,才20歲,我比他大8歲呢。呵呵,我笑,愛情不在乎年齡的。
要學漢語的是個華人,給我的第一印象有兩個,一是喜歡毫無表情的「呵呵」兩聲作答,從臉上看不出喜怒哀樂,有些木訥;二是喜歡留長長的指甲,看上去很乾淨,甲殼圓潤飽滿,修剪得也精緻,真可用削蔥尖來形容,習慣用大拇指居中那個關節發短信,以至於右手拇指比平常人要翹得多。
D介紹,他叫L,我問中文名,B說了串普通話音標里從沒出現過的音,D也一臉茫然,只好作罷。D說L還不會漢語,要從頭學起。那天到D家開的中餐館後邊的泳池兼像館搬兩把椅子教學的。
從bpmf開始,他是我第一個從起點開始教起的學生,兩個多小時下來,感覺極端疲累。之後一起吃飯。他記下我的空餘時間,說是希望每天都學,想快快地會說,只要有時間。他確實是個很用功的學生,起碼在我教的學生里最勤奮,最用心。我問他學漢語的動機,他只說,自己是個華人,不會華語很害羞,我不解小時候不學,現在才學?他說父親說福建話,母親說潮州話,在家裡都說本地話的,加上那個時候華校被封,當地禁止學漢語的,只有少數家長偷偷在家裡教子女。我嘆,悲哀!
車子開到出租房門口時,D說,L問我如果周末有時間可不可以一起到外邊遊玩並在外留宿,一邊學漢語,我說可以啊,反正我閒着。隨即付了課酬,道別。
一個星期過去了,這個說要天天學漢語的學生也不見聯繫我一次,這些生意人就是那麼忙。上個月也有一個大老闆說補習,那天上了兩個小時,過後去高級中餐館請我吃了頓大餐,末了給我三百元,我美得不行,可那以後就失蹤了。我想這個L也一樣吧,反正第一次課酬已經給了。
兩個星期後的周六晚上,就在我已經要忘了那個長指甲男人的時候,他來電話了,問可不可以一起吃晚飯,說剛下班。十分鐘後我坐在他車裡,他給我解釋着,最近接了個新的工程,很忙,都沒時間補習了,有時從早7點一直到晚11點才回家,今天叫我吃飯是希望可以維持聯繫,否則時間長了就斷了,也不好意思再聯繫了。我笑笑,沒關係,何時有空何時補都行,只要我還在。他又面無表情的呵呵兩聲。我側頭看了看他,突然發現側面的他顴骨處的皮膚膚色及毛孔形狀有些像凱,於是愣了愣。他轉過頭,呵呵,又是兩聲。我不好意思的把目光撇正。他帶我去吃這裡有名的乳鴿,吃飯時我一邊指着桌上的餐具教他些詞彙,他很用心的記。
坐下前L用紙巾幫我擦了座位和桌子,餐具上來後又用紙巾先擦拭了一番才遞給我。開吃時我發現他是我在這裡唯一見過的不用手的人,雖然很多華人吃手抓飯時還是用叉匙,但遇到雞啊什麼的一定是用手幫忙的了,他卻把個叉匙用得恰到好處,兩半一烤一煮的鴿子被他庖師般的技藝分解了,還把最好的肉給了我,我不禁對他有了點好感。是個很講衛生又懂得體貼的男人。
那天晚上居然夢到了這個白皮膚,小眼睛,長指甲,和有着與凱相似的顴骨處毛孔的男人,醒後發覺自己很花痴。凱,為什麼一個細節我都忘不了?
第二個星期六他又來電了,六點,天已全黑。上了車他問我又沒去過S市,想不想去走走?說要去見個客戶。如果同意當晚出發,次日一早他會客戶,然後帶我一處轉轉就回。我想了想,問怎麼不早說,要知道我直接收拾東西了。他說電話不好交流,也是,語言不通,說話都是三分英語三分本地話再三分身勢語外加一分漢語,只能見面談。
到了S市時已經夜裡十一點半了,進了房才知道,只有一張大床,我指着問,一張床?他呵呵兩聲,有點尷尬的樣子,指指,「你這邊,我那邊。」我哦一聲,放包,鎮定。
這裡的人似乎沒有過夜生活的習慣,開車兜了N個來回都不見一家餐館還在營業,只好進了麥當勞。有幾個美眉露腿露臍又露半個屁屁的坐在我們旁邊,身材還不錯,我不禁多看了幾眼,轉眼處發現L也在瞄另一側剛進來的兩個美眉,於是心裡笑笑,男人,呵呵。
臨睡前我故意洗了頭,想等他睡了再躺下去,蜷在大床邊緣用一半被子裹嚴了全身看電視。他卻滾了過來,伸出手為我抖弄濕發,一邊吹着氣。我轉頭,沒關係,不用了,我自己來就好,謝謝!先睡吧。他不理,依然。固執處有些像凱,憶起從前浴後凱在身邊用吹風機為我吹發的情景,我也就任着L的好意,多久沒人這樣關愛我了。
只記得,那夜L很溫柔,他有凱的成熟靜默也有F的一點點孩子氣,我的母性和情慾都被他喚醒了。天要亮時他俯在我手臂里睡去,像個孩子。我盯着他顴骨處大大小小的毛孔,發呆。那一夜他學會了一個中文單詞「睫毛」,於是配上原先就會的「長」字,他稱我為「長睫毛」,「老師」二字從此消了影蹤。
(九)無愛
L常常跑外市見客戶,我則常常推了家教隨他去。他給的溫暖和關懷讓我着迷。我需要有人疼,哪怕是暫時的,哪怕是逢場作戲。
L真的很忙,有時我都會心疼他,睡前我幫他按摩,就像當年心疼凱一樣。L總是拉住我的手說,沒關係,這樣你會累,手會酸的,別弄了。每每這時,我在感動之餘就笑自己白痴般的倔強,對誰都會心生憐憫。似乎應了凱那句話,別人把我賣了我還替別人數錢。凱是看透我的傻才離開的的吧?我想。
很多時候,一個一個的白天都是我獨在賓館上網或看電視。L總是一早就出門,晚上黑了才回來,然後帶我去吃飯。我只是靜靜靜靜地等他。他曾和我說過,女人如果希望嫁一個又有錢又能時時陪自己的老公,那就是發瘋了。何況我只是他的老師兼情人,我還沒有瘋。
我們的相處很安靜,靜得好像彼此不存在,任何的接觸似乎都遁入了虛空。只是我們暫時需要,而對方剛好可以填補。我在清醒中迷茫。常常一覺醒來不知身在何處,看着兩個赤裸裸的身軀在白色的床單上寫着獸慾的放縱,就忘了自己曾經有過的靈魂。
慢慢的,習慣了有他。每次從外城回來不見面的時候,我都會給他短信,L從沒有回過,我不知道是忙是不方便還是除了肉體我們什麼都沒有。可每次他約,我都欣喜地收拾行裝坐上他的車,看他的顴骨,握他的手,就像曾經在凱的車裡一樣,只是那時凱在左我在右,而今反向。
我常常思考自己於L的功用,一來可以學華語,二來可作性工具,三來可以解解長途一人開車的乏悶。我會是第幾個呢?為什麼男人都這樣?大概因為有我這樣的女人吧,呵呵,我笑。L轉頭看我,呵呵,面無表情。
一夜完事後,我貼着他,裝出純純的嬌氣:「我好害怕會愛上你……」L圈住我,「可是我已經結婚了。」我愣,愛和婚姻有關?於是惱回「知道,又不要嫁你!」說完滾一邊去。L靠過來,拉住我的一隻手說,「這不是愛情,愛情不是這樣的,愛情沒有這麼舒服,愛情沒有這麼甜蜜……」我轉身摟住他,輕輕一笑「嗯,知道了,我們之間沒有愛情。」
那夜我的心有點痛……
標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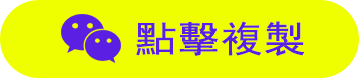




評論列表
文章我看過,感覺說的挺對的,有問題的話可以多去看看
如果發信息不回,怎麼辦?
被拉黑了,還有希望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