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手裡捏着一張單薄的火車票,穿過半月形的售票廳走到門口,抽出一根煙點上。
平常姍姍是不允許我抽煙的。姍姍的鼻子比狗的還靈敏,只要我的口腔里,哪怕是喉嚨深處,有一丁點的煙味兒,她都嗅得出來。然後斷然拒絕我的kiss。她的理由是,抽煙的男人老了周身會有濃重的嗆人的煙味兒加體味的混合體,讓人想到腐朽的枯木。我看着她就笑了,這個女人,不,也許只能叫女孩,說出這些話的時候完全不經大腦過濾,仿佛早已做好與我一生一世的準備,其實是忘了剛剛跟我鬧過彆扭。
我又看看手上的火車票,十幾個小時的長途跋涉,就濃縮在一張乾癟的毫無溫情的薄紙上。我的心尖銳的刺痛起來。若不是姍姍鬧得凶,我也下不了決心把她送走。其實姍姍鬧彆扭,不過就是莫名其妙地大哭而已。她把自己裹在床上,把臉埋在蠶絲被裡,開大音樂,就哭了,瘦弱的身子劇烈地一顫一顫。姍姍從來不像別的女人,發脾氣摔東西大罵。她只是一 味地哭,直哭得我六神無主。

2.
不久前我收到姍姍的短信趕回家,看到地上散亂的書本。姍姍在臥室,眼神空洞地望着天花板。我走進去,她空空的眼睛轉過來看了我一眼,然後緩緩別開,像一個沒有靈魂的安靜的精神病人。
為什麼?我拉過姍姍的手,姍姍呢喃似的問了一句。
我的喉嚨發不出聲音,用另一隻手摩挲她的臉。她的面容多麼姣好啊,此時卻蒼白得像一朵黯然失色的百合。
她輕輕拿開我的手,背過身,倒在床上。把臉埋在蠶絲被裡,瘦弱的身子劇烈的一顫一顫。我抱住她,試圖穩定她的情緒。以往我這一招總能奏效,可這次沒有。
還有一個月就到中秋,可姍姍神情疲倦,食量驟減。她很少和我說話,也沒有再去打理散落在地上的書本。
我毫無辦法,所以,只好給她買了回去的火車票。
3.
姍姍開始變得焦慮,在房間裡走來走去,卻不知要尋找什麼。她撕碎了火車票,從窗口丟到馬路上。
姍姍有輕微的抑鬱症。據她說是從大學畢業論文答辯那時開始的。論文,畢業,找工作,母親意外逝世,把她的神經壓崩了。她是這樣對我描述的。
那還是兩年前。我從島城到廣城,混着一份雞肋般的工作。姍姍剛剛畢業,在我隔壁租了房子。我從來不關心隔壁住了誰,可有一天姍姍來敲門,問我能不能把電飯鍋借給她。幾天後她來還我電飯鍋,說,不好意思我忘了還。我看着這個清瘦的女孩,無可奈何。
我們都是慢熱的人,漸漸熟悉也是幾個月後的事。我知道姍姍最擅長煮廣式綠豆沙,喜歡在綠豆沙里加紅糖和蜂蜜。認識姍姍之前我從不吃甜品,但每次姍姍問我吃不吃時我都會馬上回答吃。
這樣的關係要發展成情侶似乎是老套又理所當然的事情。可事實並非如此。姍姍有男朋友,在海城。但我常常聽見她的房間內死寂一片。下班回來她極少打電話,很少說話,更少上網,若非煮了我一份綠豆沙,幾乎不會來敲我的門。
那天她煮好綠豆沙帶來我房間,接了個電話,片刻,一言不發就掛了。
又死了一個。姍姍說。
我大驚,又死了一個?
呵呵,又有一個人要離棄女友和別人結婚了,所以這個世界又少了一個人。
她臉色慘白,拼命在臉上擠出一種叫笑容的東西。她輕輕吮吸着碗裡的綠豆沙。我忍不住伸手撫摸了一下她的頭。
啪。一聲脆響,我的左臉挨了有力度的一巴掌。
你以為你是誰?!姍姍怒視着我。
我騰的站起來。我連父母的巴掌都沒挨過,何況女人的。眼前這個女孩的一巴掌讓我氣惱。我拉過她,緊箍在我懷裡。她想掙脫,但力氣小得可憐。她對着我的肩膀狠狠咬了一口。
姍姍跑了。我肩膀上幾個淤黑的牙齒印都化了都沒再看見她。
兩個月後我打了個電話。對方是個講廣東話的男子。他遲遲疑疑的,問,姍姍?
我說,我不是姍姍。我撿到了這部手機,很久了,不過它的主人一直沒來認領,你知道她的地址嗎?
我也不知道她現在的地址,我們很久沒聯繫了。
明明這個男子在電話簿上的名字是老公,他卻告訴我他們很久沒聯繫了。
三個月了,姍姍連一個電話都不打。三個月前她失魂落魄的逃跑,把手機落在我這裡,此後不聞不問,水蒸氣般消失了。
我想煮綠豆沙,卻發現還沒向姍姍學過。我坐下來,卻發現對面的凳子是空着。我替她交了房租,房東開門讓我替她整理東西。房間凌亂但簡單,衣服齊整地掛在柜子里,牆壁上貼滿卡通畫,連丟在床上未來得及收好的內褲上也是卡通畫。
4.
過完中秋,島城早晚的涼氣貼上皮膚已經有點寒氣了。
清晨我醒來,看躺在我懷裡安靜呼吸的姍姍,臉很白,是一種病態的白。
那時她的抑鬱症剛剛好一點。她並沒有出走,而是回了家,靠看心理醫生和靜養過了幾個月。她稱為老公的初戀男友,為了留在海城,把原本給她準備的鑽戒戴在了別人的無名指上。
鑽戒這東西,人盡可戴。有人戴上只一兩天,有人戴上就是一輩子。
我忽然無比失落。姍姍,你認為的愛情,是什麼樣子的,它真的會讓你丟了魂嗎。
我打算回島城,然而就在我打算回島城前天,有人敲門。竟是姍姍。
姍姍說,我回來搬東西,才想起手機當時落在你這裡了。
我說,姍姍,你跟我走吧。
姍姍默默盯着我襯衣上的紐扣看了一會兒,問,經過海城嗎?
我們可以先坐火車到海城。我說。你可以在車上慢慢考慮要不要去找他。
然而後來姍姍並沒有去找她的初戀。她跟着我從火車站出來,一眼看到赫然幾個艷艷的大字:海城不夜城。她呵呵呵呵地笑了起來,不夜城不夜城。然後哭了。哭完對我說,我們走吧。
5.
清是我的前妻。我們有個孩子。
但孩子是清的前男友的。那個男人因貪污被關進了監獄。清和我在一個朋友的聚會上認識,我們相談甚歡。我喝了不少,第二天早醒來發現和清躺在同一張床上。
清長着一張無辜的臉。而那時我太年輕,總是輕易被女人清純的臉蛋所迷惑。清和我在一起沒多久就有了孩子。她一口咬定孩子是我的。於是我們結了婚。幾年後那男人出獄來找清,清指着他讓孩子叫爸爸,我才如夢初醒。
自那時起,我有點輕蔑女人。我毀了所有和清有關的東西,去了廣城。
我以為關於過去的一切證據都已經被消滅。有了姍姍,什麼都可以重新來過。
我帶着姍姍去海邊散步,去看銀杏樹,泡桐樹。她學梁朝偉的樣子,對着泡桐樹的樹洞,說了個秘密,然後把樹洞堵住。她會拉着我的手,指着路邊的一朵薔薇,說,好美的花。然後仰起臉看着我的眼睛孩童般地微笑。她還會買來核桃,一顆一顆砸開了,煲核桃仁粥讓我喝。
姍姍還沒完全好起來,但至少她莫名其妙地哭泣的次數在減少,臉色也粉起來。如果生活可以一直這樣,也許姍姍可以永遠擺脫抑鬱,也許我們會相濡以沫到老。
可那天她給還在上班的我發了短信,你妻子來找過我,她跪下來求我離開。
我眼皮一陣跳,一路奔着回去。我該怎麼對你說,姍姍,那是一塊醜陋的傷疤,是最敏感的疼痛神經。
6.
解釋都不如事實來得真實。姍姍還是決心要走。她說只要想起那個來找她的女人哀傷的臉,她就心痛得蹲下去抱着胳膊。她把新買的車票攥在手心,坐在窗邊看樓下馬路上車來人往。
她曾站在這個窗口邊問過我,你有什麼瞞着我嗎?
我很乾脆地答,沒有。
如果有一天我發現你欺騙了我,怎麼處置你呢?
隨便你怎麼處置。
要是我從這個窗口跳下去呢?
我突然醒悟過來,姍姍不會直直地反擊背叛她的人,但她也許會用自我傷害來達到懲罰的目的。傻女人。她企圖用這樣的極端留住別人對她的愛,孰知別人轉過身後依然夜夜笙歌。
7
姍姍走的時候沒有回頭。
她說她從此不能回頭望,一望就是傷。
我從車站出來,突然烏雲翻滾,下了秋後的一場雨。默默點了一根煙,煙霧散在雨霧裡,世界一片混沌。我撥姍姍的電話,電話已關機。我終於知道,這裡,終究剩下了我一人。
標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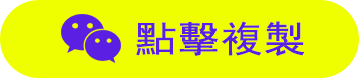




評論列表
挽回一段感情就是挽救一個家庭。
老師,可以諮詢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