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聲》 作者:易木珄
編輯有話:
我們在徵稿,過稿率超高;稿費30元-70元/篇,字數:3000-10000字
喜歡寫文的小朋友快加入我們吧!

01
我以為我的生活會一直這樣,乏善可陳,波瀾不驚。
任憑生命的河流靜靜流淌過一望無際的原野,不見驚濤,亦無駭浪。
平凡而寡淡的青春里,未嘗奢望遇到青澀卻刻骨銘心的愛戀,堅信簡媜書中所說的:「人生啊,如果嘗過一回痛快淋漓的風景,寫過一篇杜鵑啼血的文章,與一個賞心悅目的人錯肩,也就足夠了。」
所以我從來不曾設想過,十七歲的尾巴上,會有一個乾淨含笑的聲音光顧我的名字:「秦羽芹。」
從那一刻開始,漫天星辰皆黯淡無光。我後來走的每一步,似乎都只是為了追尋那個遙不可及的人。
02
高二的那個暑假,我去當了A區血站的志願者,在無償獻血過程中引導那些獻血的愛心人士,並做好後續的資料統計工作。
傍晚所有工作收尾的時候,我突然發現其中有個人的必填信息有所缺漏,便順着聯繫方式發了短信,那邊一直沒有回覆,我草草扒了幾口快餐,重新翻出那個號碼撥了過去。
第三聲「嘟」剛剛響完,一個純淨溫潤的年輕男聲闖入我的耳朵:「你好?」
我的心突然像卡殼了的跳跳蛙,撲騰出陌生古怪的節奏,不得不咬了咬舌頭,結結巴巴地說:「您,您好!這裡是A區血站,今天下午您來獻血有項個人信息有誤,能不能……麻煩您重新說一遍?」
對方似乎有些心不在焉,但仍然耐心地幫我完成了工作。臨了,我突然腦子一抽,極為笨拙地強行插了句:「趙先生,我叫秦羽芹。」
對方愣了一下,頗為無奈地一笑:「好的。再見,秦羽芹。」接着掛了電話。
我聽着那頭的忙音心跳徹底紊亂:活了十七年我才發現,原來我的名字,可以被念得如此好聽。
宛如一縷神的光芒輕撫在路旁的石塊上,那麼這塊普通的石頭,便被賦予了意義。
我普通而大眾的名字,經由他的重複,據此獲得了新生。我摸着自己有些發燙的臉頰,突然明白了為什麼被小王子馴服的狐狸才是獨一無二的。我,秦羽芹,自以為沒長戀愛腦的木頭,就這樣以一種莫名其妙甚至有點搞笑的方式,被馴服了。
但我並未想過與這個名為趙寒的年輕男生有什麼更深入的接觸,茫茫人海本就難尋蹤跡,況且我也無意於此。
只是世事往往出人意料,我們居然很快有了新的交集。
03
每年十月底學校都會舉辦為期一周的藝術節,本就是一場盛會,而與往常不同的是,這次正逢六十周年校慶,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主任坐在辦公室的椅子上,一本正經地給我強調會有很多領導參加開幕式,學校非常重視此次的活動,所以。
「所以,這次的開幕式主持詞的寫作任務就交給你了,一定要高質量完成!」主任放下手裡的筆,正襟危坐地給我下達了指令。我不忍辜負他過分鄭重地眼神,咬咬牙接下了這個燙手的山芋,內心哀嚎。
我成績並不好,上高中後甚至可以稱得上慘不忍睹,唯有語文從小到大穩居第一,長期舞文弄墨甚至還小有名氣。是以,這樣的任務總會讓我來組織完成。
趁午休的空當,我拿着主任給我的策劃書與流程單,先去找流程組的同學敲定分工。看到主持人名單上的「趙寒」二字,我愣了一下,嘀咕道:「趙寒?今年的主持人是新生嗎?」
身邊的小七怪叫一聲,以一種看原始人的眼神盯着我,渾身上下寫滿了不可思議:「不會吧芹芹!你怕不是今天才轉學過來的?」
我咽了口唾沫,老老實實承認自己真沒聽說過他。
小七恨鐵不成鋼地抽了一下我的腦袋,一邊左顧右盼探查老師的身影,一邊忙不迭掏出手機給我翻照片:「趙寒跟咱們是一級的好不好!人家可是大名人呢,不僅是學生會副主席還是廣播台台長。你還在看動畫片的時候他就去電視台主持少兒節目了,咱們學校的明星招牌啊!噥,你自己瞅瞅,說是校草也不為過吧?」
我接過她的手機,屏幕上是一個穿着白襯衫低頭看書的男孩子,雖然偷拍畫質不清,卻仍然能看出男生輕拈書頁骨節分明、白皙修長的手指,金絲邊眼鏡下恬靜溫潤的臉,莫名使人感覺內心安寧。雖談不上過分精緻,卻自帶屏蔽喧囂的氣質,清雅絕塵。
彼時的我還不能確定他就是那個人,卻下意識對見面多了幾分期待。
初稿敲定的那一天,我坐在窗邊的位置上打着哈欠沖咖啡。外面忽然一陣騷動,文科班的女生們向來如此,我下意識瞟了一眼門口,只見幾個女生故作矜持地捂嘴大笑,用誇張到變形的語調問:「秦羽芹?主席確定不是來找我的?」
搞什麼。我皺皺眉,看着不小心撒在桌面上咖啡粉,頓時感到肝氣鬱結,顧不得其他。同桌嘻嘻哈哈地撲過來扯我出去,我看見了他。
周遭瞬間安靜。
用不着開口,我就知道,趙寒只有一個,獨一無二。
他打量着我,突然「噗嗤」笑了出來,頗為假正經地伸手:「秦姑娘,我叫趙寒。」聲音一如既往的好聽。
我故作熟稔地瞅了他一眼,準確而迅速地伸手和他擊了個掌,指尖傳來的溫度緩緩熨帖到心裡:「合作愉快,趙先生。不如我們約個時間過一下初稿?」
他大概沒想到我這般直接,愣了一下復又笑道:「那是當然,本來今天找你就是想問問,不知道下午的課結束後你有沒有安排?」
周圍的女孩子們嘰嘰喳喳議論個不停,而我什麼都顧不得了。最後的最後,我利用自己的常年面癱臉堪堪維持了表面的穩重人設,風輕雲淡地和趙寒約定好時間地點,內心早已翻起巨浪。
04
六點。我獨自坐在一間小辦公室等他,廣播裡是婉轉悠揚的鋼琴曲,晚風拂面,旋律繞樑,倒有幾分說不出的愜意。我微闔雙眼靠在沙發上休息,一時不察被人塞了杯熱牛奶在手裡。
「趁熱快喝吧,小心別燙着。」趙寒順着沙發癱在我旁邊,扭頭看着我笑,「以後少喝點咖啡吧。」
我抿了口牛奶,把稿子遞給他,突然發現他真的很愛笑,眉眼彎彎,盈着說不出的溫柔,不知不覺之間就融化了我心底的緊張與侷促。
熱牛奶溫暖了五臟六腑,我問他:「有什麼問題嗎?」
「嗯……」他皺眉,食指摩挲着下巴,「我可不可以問一下,這個嵐……什麼,是什麼意思?」
「嵐岫?煙霧繚繞的山峰吧。」我順着他的視線看過去。
他還是眉頭緊鎖,試着讀了一遍:「『寒翠入嵐岫,暖金染素秋……』你覺不覺得有些生僻牽強?」
我在心底玩味了一下他情緒飽滿字正腔圓的播音腔,沉吟着點點頭,着手更改。
暖色斜陽從窗口偷偷灑進來,為面前的白淨少年鍍上了金色的輪廓,我們就這樣,一句一句讀一字一字改,我聽着他清朗的嗓音光顧我筆下的字句,胸口像是放進了一團毛茸茸的小太陽,暖得發癢。
改完初稿天色已黯,趙寒握着台本伸了個大大的懶腰,眯眼的神情宛如饜足的貓。
我不由自主望着他抿嘴笑。他卻一下子坐起來,認真看着我說:「原來你會笑啊?」
我愣了愣,他抬手,拇指和食指在唇邊劃出一條弧線:「以後多笑笑吧,你笑起來很好看。」
回到寢室,我躲在洗手間裡學他用兩指畫出一條弧線,對着鏡子笑。
鏡子裡的姑娘平平淡淡,唯有一雙眼睛亮亮閃閃,帶着不自覺的柔情,笑起來羞澀卻又真誠。當時的我還不知道,有句話叫:「喜歡一個人是藏不住的,即使捂住嘴巴,也還是會從眼睛裡跑出來。」
我雙眸中閃閃的光,就是喜歡悄悄跑出來的鐵證。
05
一個多月過得太快,其他三個主持人並不常出現。我和趙寒兩人敲好主持詞,便一起出去玩,關係突飛猛進,我才知道那次獻血是他給自己十八歲的成人禮。
每天我都會給他帶點心,他則送我回寢室,嬉笑打鬧之間也練就了相當的默契。我常常提醒自己要多笑,自此在班級里活躍了不少。
小七曾仔細盯着我觀察了幾圈,然後摸着下巴嚴肅地得出了一個結論:「怪了,芹芹,你最近一定有什麼好事。」我雙頰發燒,強行把話題繞開,心中微甜。
藝術節開幕之前,我在後台為他們準備好手卡,趙寒做完造型,一身筆挺的西裝,沒戴眼鏡的雙眸清澈,我不由笑得燦爛,走上前幫他理了理領子,遞給他手卡:「今天也要加油吶!」
他伸手揉亂我的頭髮,笑意從眼波中蕩漾出來:「當然,結束請我吃飯啊,不許耍賴。」我跑開拯救髮型,他在我身後嘰嘰咕咕叫着「菜菜」之類的諢名,我翻了個大大的白眼:這廝果然沒有偶像包袱。
開幕式最後的完成圓滿到出人意料。中間演出音頻出了故障,台前幕後慌成一團,而趙寒一個人搞互動熱場子,硬生生扛了十幾分鐘,神級救場讓在場所有人印象深刻,校領導集體決定給他頒獎。
散場之後,我有些矯情地熱淚盈眶,和每個工作人員認真擁抱。趙寒放回話筒,安靜地走到我身邊,四目相對,眼淚突然決堤。趙寒牽牽嘴角,緊緊地將我擁入懷中:「哭什麼啊,傻菜菜。」嗓音輕緩溫柔,身上是少年人獨有的清冽氣息。
奪目的光環之下,這個名字清冷的男孩,其實溫暖和煦得不像話。
當晚的聚餐我們都格外放飛自我,我放肆地從趙寒手裡搶烤串、搶酒、搶話筒,他一邊無奈地罵我是豬一邊又從我手裡奪酒杯,玩大冒險拼命護着我。
我其實很捨不得,我和趙寒並不在一個班,甚至不在一棟樓,這些日子與他朝夕相處,此後卻沒有了再膩在一起的理由。
悲喜之間,趙寒抽到了真心話:「有沒有喜歡的女孩子?」我低頭撇開視線,只聽他爽朗地大聲笑道:「當然有啊!我可暗戀人家很久了。」
「有多久?」
「也就比不認識她的時間多那麼幾年咯。」
頓時全場沸騰,我慌了神,心裡「咯噔」一聲,滿腦子妖魔鬼怪被炸了個乾淨。
我不是沒有奢望過什麼,哪怕給我留一點點幻想的餘地都好。
可現實就這麼殘忍,我還沒開始,就輸得一敗塗地。
06
之後的時間仿佛被繁重的課業與數不清的考試排名壓榨乾淨,情感與瑣事穿過皮囊留在過去,只能握住筆的指尖擔負不住那個少年的名字。
他依舊是文科班女生八卦中的常客:據說藝術節之後,高一新晉的校花就跟他表了白,雖然他拒絕得乾脆,卻依舊招了不少男生妒忌與非議。
總聽她們說趙寒對待女生友好但不親密,客氣之中帶着無法消磨的疏離。對此流傳着種種版本的揣測,歸根結底不過是羨慕那個將來或者已經被他放在心上的女生,該是多麼多麼幸福。
我心底總是隱隱覺得他待我不同,卻也只能搖搖頭嘲笑自己的痴心妄想,他是漫天星辰,而我不會擁有任何一顆,僅僅是安靜仰望,便花光了我畢生的運氣。
還好,我每天都會遇見他,做課間操的時候,人滿為患的食堂,甚至地方台的公益廣告代言人,我近視五百多度的眼睛自帶馬賽克效果,卻獨獨能看清他、第一時間找到他——我顏色絢爛身姿筆挺的小白楊。
神說,要有光。於是就有了他。
高三那個寒假,過年氣氛寥寥,電視自顧自播着毫無笑點的春晚,父母「體貼」地減少了我外出的機會,為高考衝刺磨刀。
座機響了幾聲,不知道那頭說了什麼,爸爸把電話遞給了我。對面混雜着爆竹的聲響,小七輕快的聲音傳了過來:「過年好啊芹芹!主任說有個往年藝術節的資料需要整理,可不可以過來幫幫忙嘛,這可是最後一次『盡忠』的機會了哦!」
我猶豫片刻還是前往了學校。
本就是過年放假,天色已晚,校園裡怎麼看都不像還有人的樣子。我正奇怪,突然有人拍了下我的肩膀,驚訝地轉身,竟然是趙寒。
「你怎麼也在這兒?」我驚呼。
他從身後捧出一大把煙花獻寶似的塞給我,笑得張揚:「我不讓小七找這個藉口,難道還能見你嗎?傻菜菜,你爸爸可是告訴我你不在家的。」
我頓時無言以對,剛伸出手揍他,他卻靈巧一躲,臭不要臉地扯下我一隻手套,哆哆嗦嗦把手往裡擠。我才注意到他清瘦了許多,穿着羽絨服依舊單薄,莫名讓人心疼。
他拉着我輕車熟路往旁邊的家屬樓里鑽,不知道摸黑上了多少層,拉開門竟鑽到了天台上。
天已經完全黑下來了,碎鑽似的星星忽明忽暗綴在夜幕上,身下萬家燈火溫馨異常,我驚呼:「你是怎麼發現這種地方的啊?」
趙寒接過煙花開始點燃,有種回到童年的錯覺。「以前在這裡補過課,心情不好逃課上來透透風。」他狡黠地眨眨眼,笑着說。
他負責點,我躲在安全的地方看,我倆吵吵鬧鬧笑作一團,看各色煙花在夜空綻放,轉瞬即逝,備考的壓抑情緒一掃而光。
等全部放完,趙寒扒在欄杆上,夜色籠罩下他的五官柔和且神秘,扭頭誠懇地問我:「你願不願和我一起去北京?」他的眼睛亮亮的,閃爍着清澈的光。
「去北京?」
「是啊,去北京。我明天就要過去參加藝考了,很抱歉現在才告訴你。」
「那……祝你一切順利!主席永遠是最最最厲害的!」我有些躲閃,不太想看見他眼中明明滅滅的光,裝作若無其事看着欄杆上的一塊鐵鏽呢喃:「我從小,就特別喜歡北京。」
少年開心地歡呼,雙手比成喇叭放在嘴邊對遠處喊:「北京!我們來了!北京!我們來了!北京……」一遍一遍,不知疲倦。
我咬着下唇對他微笑,眼睛裡流露的是自己都不知道的眷戀。
那天的最後,我和他擊掌:「期待你的好消息。」
而沒有說出口的是,家裡人其實早已為我安排了一所英國的大學,所有手續都已準備妥當。留在這裡高考,只不過是我能為自己爭取的最後機會。
我和我的少年,還有不到四個月。
07
最後一學期毫不客氣地到來,明明萬物復甦春暖花開,我卻更懷念那個寒冬的夜晚,那個刮着冷風的房頂。我把自己埋進習題堆里,持之以恆地自欺欺人。
趙寒的藝考成績相當優異,大紅的喜報掛在校門口異常耀眼,無疑是老師重點培養的人才。他不再明目張胆地出現在我們班門口引起尖叫,但總會隔三岔五讓別人幫忙遞東西給我,有時候是一杯檸檬茶,有時候只是一張寫着勵志字句的卡片,上面都無一例外地畫着一個草率的笑臉。
我不知道怎麼回報他,只好木訥地說句謝謝,心裡恨極了自己的懦弱。然後坐到座位上認真到近乎虔誠地將寫着他遒勁有力字跡的卡片貼在筆記本的內頁,而前面,寫着他的生日和手機號,貼着每一稿台本,以及一個小小的「北京」。
這是我堅持下去的唯一動力。
高考倒計時一個月。
陽光灼熱,氣溫躁動,初夏大張旗鼓地在每個人耳邊聒噪。
午休時間在班裡學習的同學越來越多。某天我吃完午飯剛進門便有人傳話:班主任叫我過去。
教室里里氣氛有些微妙,平時愛八卦的女生聚成一團竊竊私語,時不時有試探的眼神落在我身上又轉瞬即逝。我不敢追問,心裡惴惴地,有種很不祥的預感。
辦公室里只有幾個老師,我一眼就看到了那個本子,那個負載着趙寒的期許與我的奢望的筆記本,此時正醜陋地攤在班主任桌子上。果然。
「我……」我慌了神,低頭不敢直視老師們的眼睛。只能死死盯着白鞋上不知道從哪裡蹭到了一塊污漬,仿佛它扎進了我的血脈,風捲殘雲般吞噬着我近一年借來的所有勇氣。
班主任扶扶眼鏡,鏡片折射出幾分犀利的光,冷冰冰地開口:「秦羽芹,有些事情我們都心知肚明。也許你有退路,但趙寒一步都不能走錯。
「你們都還承擔不起自己的責任,哪能有什麼未來?
「老師希望你能看明白現在的狀況,不要成為他的負累……」
他們後來也許說了很多話,但我一句也聽不見了,腦子裡一直回想着「不要成為他的負累」。
原來我自以為的喜歡,早就成為了阻礙他高飛的枷鎖。
08
我開始躲着趙寒,能碰見他的場合一律躲掉,懦弱到分外狼狽。
「秦羽芹,你給我站住。」離校前最後一個晚自習結束後,趙寒忍無可忍地攔住我,聲音說不出的疲憊。
我笨拙地端着我的玻璃杯,不敢看他的眼睛,嘴角努力想裝作若無其事地微笑:「嗨,趙寒。」
他抿了下唇,放緩了聲音問我:「你就沒有什麼想對我說的?」
我聚精會神地盯着他挽到手臂的襯衣袖子,似乎上面有道難解的數學題亟需推演,騙自己從他溫度灼人的注視下抽身出來,囁嚅道:「趙寒……明天就要高考了……加油。」詞不達意,言不由衷。
他表情怪異地咧了咧嘴,無聲說了兩句什麼,擺擺手讓我回去。
轉身那一瞬間,我仿佛有所感應一般抬頭看向教室門上的茶色玻璃,趙寒的眼神正正落在我的鏡像上。兩條視線猝然相撞,手中的杯子瞬間滑落破碎,我不敢眨眼,將他眼底綿長的失望與無法言說的複雜情緒盡數接納。不過一瞬,卻仿佛萬年之長,他別過視線轉身離去。我看着地上粉身碎骨的玻璃杯,雙目仿佛失了焦,臉上被淚水浸濕。
其實聖誕節時我送趙寒的杯子,是一對。我出於私心留下了一個,卻不想當着他的面碎得乾淨。
宛如心碎。
我再也沒有見過他。
09
小七其實說錯了,趙寒並沒有當過電視台的小主持人。
有件事我沒有告訴任何人,包括趙寒。
離開家去遠方求學的最後一晚,我在家中落灰的陳年舊物中找到過一盤沒有標識的磁帶。仿佛有所感召般,固執地找了個複讀機想聽完它。
一段漫長的吱吱呀呀的噪音之後,是一個稚嫩的童音在期期艾艾念台詞,旁邊的大人着急地對她吼:「都是你自己寫的東西怎麼就不能流利讀出來呢?光耽誤工夫。去叫那個小男孩過來!」
磁帶漸漸沒了聲音,卻一直轉個不停,似乎還有內容沒有播完。我剛想伸手關了它,下一秒突然心跳停滯僵在原地:一個小男孩乾淨明亮的聲音說:「秦羽芹你別哭好不好?我去給你買牛奶。」
女孩哭得抽抽答答還死要面子:「趙……趙寒!你有本事……自己寫自己念啊……」
我想我記起來了,這樁湮滅在我人生諸多挫折之下的舊事。
小時候的一個兒童廣播節目招募小主持。參與海選的人很多,我知道怎麼串接,怎麼控場,並且乖巧懂事,本該是最好的人選。實則都不過是紙上談兵,內向所以緊張,緊張所以不成事,我直接被淘汰。而最後選中的人,是趙寒。
為了安慰我,趙寒與我拉鈎:從此他台前我幕後,要做最好的拍檔。
原來從那時起,你就出現在我的生命里了。
兩個人的回憶,只有一個人來守護,是不是太孤單了?
三年。我已經變成了曾經不敢想象的、愛笑愛熱鬧的活躍分子。期間寫過不少文字,卻再也沒有碰過一次主持稿。如果成心想忘記什麼,那與其有關的一切都可以被封為禁忌。如今,是時候告別這場自我折磨了。
我曾在偶然間發現了趙寒的個人電台,最後的更新以一封自白止步於今年六月。我明白他的意思,所以瞞着家裡回國直接去了北京。
獨自一人站在廣院的校園裡,看成蔭的白楊樹,聽湖邊開嗓讀書,走在趙寒走過三年的路上,想象他三年來每一天的生活。我會用力記住現在所遇見的每處風景,因為我們再也不會重逢。
如果我能不懦弱,現在大約已是另外一番景象。
可惜從來沒有如果。
我看明白了他最後那兩句無聲的話:
一個是「我愛你」。
另一句是「秦羽芹」。
尾聲
「如果愛要用嘴巴說出來,那啞巴該怎麼相愛。」
這是我電台朗讀的最後一句話。
還記得當時和秦羽芹一起看這部電影的時候,我嘲笑男女主,愛就愛了,孤注一擲珍惜時間在一起便是,兜兜轉轉相互辜負,才是真的「比悲傷更悲傷的故事」。
她眼淚汪汪斜着眼睛看我,搞得我似乎成了萬人唾棄的負心漢,連忙閉嘴。
後來我才知道,並不是所有人在任何時候都可以奮不顧身的。我們之間無法言說的那些部分,經由歲月的洗禮,終究成為了感情的負累。我猶豫不前錯失機會,她一聲不吭遠走他鄉。這場感情里沒有對錯,我們都是徹頭徹尾的失敗者。
我不是什麼有理想有抱負的人,從來都覺得未來是一團混沌,前路不清,去路不明。但總覺得只要有她在我身邊,萬千世界,茫茫人海,依舊有棲息之所。
藝考成績出來那一刻,我只想與她分享。我甚至希望今後我人生中每一個喜悅的瞬間,都有她的參與。然而就如同走出藝考考場後我擁抱的第一個人不能是她一樣,很多世事並不由人。她有她自己的人生,就算其中沒有我的參與,也應該繁花似錦。
我們都不夠勇敢,何必覺得遺憾?
這三年,我朗讀了她所有的文章,見證她逐漸堅強,這很好。是時候再見了,我辦好了手續,去英國,看看她生活過的國家,猜測她走過的風景。然後就此別過。
她並不會知道。就像她不會知道,我暗戀她遠遠早於她認識我;就像她不會知道,我變得優秀只為引她注意;就像她不會知道,她偶然提到喜歡北京改變了我的志向。
如果樁樁件件都要計較,哪裡還有半分喜歡的純粹。我會記得煙花照耀下她安靜的側顏,這就夠了。
我愛你,秦羽芹,最後一次。
完
投稿方式:私信諮詢
圖 | 來源於網絡 | 侵刪
文 | 初賜短篇小說
標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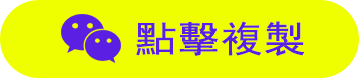




評論列表
太感謝你了,我們現在都已經和好了,謝謝!
求助
老師,可以諮詢下嗎?
老師,可以諮詢下嗎?